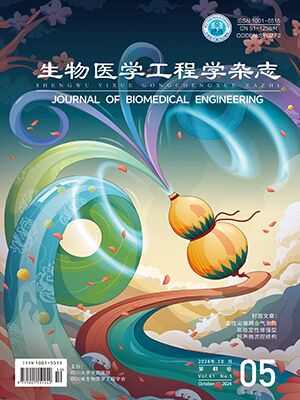视距外控制对具有大范围运动能力的生物机器人意义重大。鸽子生物机器人以在体预编程的方式实现了视距外控制,但尚未形成控制闭环。本研究在鸽子生物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神经刺激功能之上增设运动监测功能,对鸽子飞行状态实时解算,结合逻辑判据实现户外飞行过程中转向及盘旋的闭环调控。调控刺激位点位于鸽子中脑网状结构(FRM)的两侧,分别用于左向和右向控制;刺激信号具有生物神经细胞膜电位的波形特征并间歇激活;控制系统总重11.8 g。结果表明,该鸽子生物机器人的闭环调控成功率达到90%;辅以在体摄像装置,可方便获取飞行机动时的翼面形态;结合鸽群等级特征,能够实现个体调控对集群演化的干预。这些为发掘鸽子生物机器人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引用本文: 王浩, 王绍康, 邱兆成, 张琦, 许帅. 户外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设计及初步应用.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22, 39(6): 1209-1217. doi: 10.7507/1001-5515.202207077 复制
引言
生物机器人具有生物和机器的双重属性,是把生物有机体作为载体的特种机器人,是人类通过控制技术施加干预信号调控生物行为从而实现人类操控的生物[1-2]。可见,生物机器人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充分利用自然界动物在陆上[3-6]、水下[7-9]、空中[10-12]的运动能力。然而,受制于遥控遥测手段和通讯距离的限制[13],大多数生物机器人的受控范围局限于室内或室外几百米的半径内,这极大地限制了生物机器人的运动潜能和应用潜力。特别是对以归巢本能和长距离飞行为特点的鸽子生物机器人[14-16]而言,实现其户外飞行的视距外运动调控尤为重要。舍弃实时通讯,在远端控制系统直接编程控制指令,以预设条件触发固定的脑电刺激信号,为解决户外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视距外调控提供了思路[17]。这种预编程调控模式解决了鸽子生物机器人在操作人员视距外运动时如何产生控制指令的问题,但还缺乏反馈,未形成控制闭环。
另一方面,随着生物机器人技术的日趋成熟,发掘这项技术的应用出口已提上日程。除了侦察与救援这一热门应用方向[18-19],把生物机器人作为人工可控的科学工具,用于动物个体及集群的运动、协调、交互等各类行为机制及仿生应用的研究[20-22],也逐渐受到重视。
鸽子生物机器人已经具有了可靠的微电刺激~运动响应范式,在80 Hz正负双相电压刺激脉冲的作用下,通过调节刺激脉冲占空比、脉冲序列的长短及周期性间隔,可以实现转弯、盘旋等多种飞行动作的控制[17, 22],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本文针对鸽子生物机器人发展和应用的需求,采用逻辑调控思路,依托神经调控原理和脑机接口技术,设计了一种可实现户外飞行闭环控制的鸽子生物机器人,并展示了该机器人在扑翼飞行和集群协调等研究领域的应用。鸽子背载的控制系统中预设机动任务,如在特定区域或时刻开始转向或盘旋;系统借助北斗导航模块对飞行轨迹实时监测,并解算当前飞行状态;依据调控逻辑触发控制指令,发送脑电刺激信号;判断机动任务的执行情况,并形成下一步指令。
1 闭环控制系统
1.1 系统逻辑
自然界鸽子飞行能力较强,具体表现在:飞行距离远,一般在十公里以上[17];飞行速度快,平均时速约60 km/h[17],短时间内爆发速度可达100 km/h;巡航飞行高度约为150 m,同时个体负载能力有限。鸽子飞行的这些特点限制了现有生物机器人通讯技术[13]在鸽子生物机器人上的应用,尤其在户外远距离场景下,无法构成地面端人工监测中心和远端鸽子生物机器人的控制闭环。本文提出,在生物机器人背载设备的神经刺激功能之上,增加运动监测功能,以在体机器监测替代远端人工监测,用逻辑算法实现生物机器人的控制闭环。运动监测功能的实现依托全球卫星定位导航技术[23],选用外形小巧、定位精度更优的国产北斗模块[24]。模块设置了最高时间分辨率(5 Hz),以满足快速飞行采样的要求。鸽子生物机器人闭环控制系统的逻辑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鸽子生物机器人闭环控制逻辑流程
Figure1.
Logic flow of the closed loop control in a pigeon-robot
图1
鸽子生物机器人闭环控制逻辑流程
Figure1.
Logic flow of the closed loop control in a pigeon-robot
1.2 软硬件设计
我们设计的鸽子生物机器人的整体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其中,在体控制系统包括中央控制模块、运动监测模块、神经刺激模块、数据存储模块;脑机接口是控制系统与鸽脑的连接;马甲或背贴用于控制系统的穿戴或背载。图中箭头表示数据流向,实线段表示物理连接。中央控制模块主要由嵌入式系统中央处理器STM32F103RBT6和电源管理芯片RT9193、TC7660EOA组成;运动监测模块由北斗导航单元ATGM336H和无源陶瓷天线组成;神经刺激模块由中控的GPIO与运算放大器MC33202组成;脑机接口结合鸽子颅骨特性设计[25]。
 图2
鸽子生物机器人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ure2.
System diagram of a pigeon-robot
图2
鸽子生物机器人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ure2.
System diagram of a pigeon-robot
1.2.1 系统硬件
系统硬件的电路原理如图3所示。中央控制模块的核心是STM32F103RBT6芯片(意法半导体),工作时钟最高为72 MHz。在KEIL开发环境(Keil Software,美国)下编译成功的控制程序贮存在芯片存储器中。当系统上电后,芯片根据设定的时序依次在存储器中调用程序,设置相应的数据寄存器,并配置输入输出端口。控制程序从外周设备读取数据,通过运算模块对数据进行代数及逻辑运算,并依据运算结果形成输出指令,产生下一步操作。中央控制模块由一片锂电池(3.7 V,400 mAh)供电,可以持续供电4 h左右。电源管理包括稳压电路、负压转换电路、抗干扰及过压保护电路。稳压电路选用RT9193,产生3.3 V恒压为系统各模块供电;负压转换电路选用TC7660EOA,为双相脑电刺激信号提供负压;抗干扰电路采用滤波方式以减轻来自电源的耦合干扰,过压保护电路避免电路中突然的过压烧坏元器件。另外,中央控制模块预留接口,用于功能扩充。
 图3
控制系统电路原理图
Figure3.
The circuit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trol system
图3
控制系统电路原理图
Figure3.
The circuit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trol system
运动监测模块采用商用北斗模组ATGM336H(中科微电子,中国),其灵敏度高,支持BDS、GPS和GLONASS三种卫星导航系统的单系统定位以及任意组合的多系统联合定位。模组的配置可在PC端使用GNSSToolKit工具实现,设置上限采样率(5 Hz)以匹配鸽子的飞行速度,同时设定UART接口RXD/TXD的波特率为15.2 kBit/s;为减少数据传输量,按NMEA-0183协议仅选择$GNRMC帧信息,输出仅包含经度、纬度、高度及时间信息的BDS定位数据。运动监测模块与中央控制模块通过SPI协议进行数据传送,电气上直接与PA9(TXD)和PA10(RXD)连接。
神经刺激模块由中央控制模块的GPIO输出与运算放大器MC33202共同组成。主控程序产生脉宽可调的PWM信号,其中一路不作分压处理,另一路通过电阻分压降低信号幅值,两路信号经由运算放大器MC33202进行减法运算,可以产生幅值与脉宽灵活多变的双相脑电刺激信号。
数据存储模块由TF卡及其驱动电路组成。TF卡存储容量可达8 GB,可记录实验过程中的各类数据。数据存储模块通过SPI总线与中央控制模块连接,以DMA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脑机接口在文献[25]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通过脑机接口植入两根刺激电极和一根参考电极。刺激电极的目标靶点位于鸽子中脑网状结构(formation reticularis medialis mesencephali,FRM)的左右双侧,即以耳杆连线中点为空间坐标系原点,矢向取3.0~3.6 mm,冠向取1.0~2.5 mm,纵向取4.0~6.5 mm;参考电极置于头部皮下的一侧颅骨上。
鸽子生物机器人控制系统(见图4a)的外形尺寸为30 mm×30 mm×12 mm,含电池重量为11.8 g,其背载方式有背贴式和马甲式两种。背贴式即在鸽子左右翅根之间的背部区域、背载设备的底面,分别粘贴尼龙搭扣的两部分,该方式背载、脱离方便,适用于一体化的背载设备(见图4b);马甲式即用弹性布料量体裁制组合式马甲(见图4c),可套头穿戴至胸腹部,在马甲上可以穿引导线用于电气连接,适用于分布式的背载设备(见图4d)。
 图4
硬件实物图
图4
硬件实物图
a. 控制系统;b. 背贴式背载;c. 马甲;d. 马甲式背载 (彩图)
Figure4. Photos of pigeon-robotsa. control system; b. wearing by Velcro; c. pigeon vest; d. wearing by vest
1.2.2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在KEIL开发平台编辑、编译和调试,确保工作流程(见图1)的执行。软件除了驱动系统硬件、协调外周模块等次要功能外,主要功能是实现鸽子生物机器人的逻辑调控:一是利用运动监测模块硬件获取的实时坐标数据分析飞行调控任务执行情况,二是结合神经刺激模块硬件构造双相脑电刺激信号。
运动监测模块实时获取当前地理经纬度坐标,并依据WGS-84系统规则把经纬度坐标转换为笛卡尔坐标(以鸽舍为坐标原点),以当前时刻坐标与上一时刻坐标的矢量差解算当前的飞行速度与方向。当飞行调控任务启动后,令脑电刺激开始前的飞行方向为参考方向;之后每施加一次单元刺激序列(见后文定义),进行一次飞行方向解算,并与参考方向比较获得飞行偏角;以飞行偏角的数值判定任务是否达到预期。对于转向任务,设定具体的预期偏角;对于盘旋任务,以飞行偏角超过±270°(+代表左盘旋,–代表右盘旋)为判据,此后即使没有后续刺激,鸽子也会本能地继续转向,以回归刺激前的飞行方向。
神经刺激模块输出的单元刺激序列为一时长4 s的脉冲串信号,前2 s为刺激脉冲串,后2 s为零电平,以避免持续电刺激对脑组织造成损伤。刺激脉冲串的频率为80 Hz(周期12.5 ms,由系统72 M主频、1 000分频、900重装载值决定),刺激波形由中控GPIO产生的两路PWM波经由运算放大器减法合成,产生正负幅值比例、正负脉宽比例均可调的双相刺激信号(见图5a)。单个刺激脉冲的波形仿照神经细胞动作电位设计。神经细胞动作电位(见图5b)包含一个细胞膜电位快速由负电位上升至正电位然后回落的过程。由负升正段由去极化(图5b中b-c段)和反极化/超射(图5b中c-d段)构成,过程陡峭,此时膜内的负电位迅速消失并继而变为正电位,膜内外电位差快速升高;回落段由复极化(图5b中d-e段)构成,过程相对较缓,膜内外电位差逐步回落,并最终恢复至静息负电位。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脑电刺激信号按照上述膜电位生理过程设计,在刺激目标靶区用较短的时间施加较大的负电压(–3.3 V)以注入负电荷,然后用两倍的时间施加较小正电压(+1.65 V),形成模拟动作电位的刺激信号(见图5c)。在软件中调整PWM的占空比和脉冲幅值,使PWM1的幅值是PWM2的一半,而脉宽是其两倍,且满足相位关系,即可实现单刺激脉冲的合成。单元刺激序列则是由160个单刺激脉冲组成的连续刺激脉冲串。
 图5
脑电刺激信号设计
图5
脑电刺激信号设计
a. 双相刺激信号合成;b. 神经细胞动作电位;c. 示波器显示的单个刺激脉冲
Figure5. Design of the brain stimulation signala. synthesis of biphasic signals; b. action potential of nerve cell; c. stimulation pulse in oscilloscope
2 动物实验和结果
动物实验所用的鸽子,在当地信鸽协会的指导和监督下,由课题组自主饲养和繁育。实验选用两只月龄6个月以上的成年鸽,体重范围在400~500 g之间。经外科手术植入控制电极并安装脑机接口的鸽子生物机器人在恢复3~5天后,进行室内和户外运动调控测试。室内测试的目的是检验调控的有效性,并确定户外测试所需的脑电刺激参数。户外测试在合适的天气条件(晴天、微风)下进行。鸽子生物机器人于10 km外独自归巢,约10 min的飞行行程。为避免起飞和降落阶段的自主飞行机动影响,逻辑调控在行程中段进行,时间窗口有限,仅调控左、右盘旋各一次。实验共进行5次,分别在5个上午进行。在室内和户外测试确认了鸽子生物机器人飞行调控有效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测试了鸽子生物机器人的两类应用能力:一是同步获取自身机动飞行轨迹和翼面形态的能力,二是干预影响所属集群决策和演化的能力。前者通过单只鸽子生物机器人展示;后者由1只鸽子生物机器人和2只自然鸽构成的集群展示,其中自然鸽的月龄和体重与鸽子生物机器人相当。
2.1 室内测试
室内测试鸽子生物机器人在1次单元刺激序列作用下身体转向的角度,并在调控有效的前提下确定脑电刺激脉冲参数。刺激脉冲的脉冲频率及正负相电压幅值恒定不变,可变参数仅为刺激脉宽P。由于正负相脉宽比例恒定,以负相脉宽定义参数P,取值范围在0.014~4.167 ms,变化步长近似为0.014 ms;正相脉宽是负相的2倍。测试以两分钟为间隔,逐步增加刺激脉冲的P值,直到该脉宽的单元刺激序列能够诱导出鸽子原地转向360°的动作。即,确定诱导鸽子原地转向一周所需的最小脉宽值,为后续户外测试所用。对左右脑目标靶区的刺激参数采用相同的方式确定。
全部室内测试均实现了鸽子生物机器人原地360°转向诱导,所需刺激脉宽如图6所示。可见,不同个体、不同脑区的刺激脉宽有较大差异,这是由动物间的个体差异以及电极植入位点的定位误差所致。另外,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为实现相同诱导动作所需的刺激脉宽P也在逐渐增大。生物组织对侵入的异物会产生自然的排异反应,从异物尖端开始逐渐产生包裹层。随着电极尖端触点周围包裹层的日益增厚,其组织阻抗增大、电传导性变差,同等强度刺激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为达到相同的刺激效果,需要增大刺激强度。一般而言,植入刺激电极后的两周至一个月内,是鸽子生物机器人最佳测试时间。
 图6
刺激脉宽
Figure6.
Pulse width of stimulation signal
图6
刺激脉宽
Figure6.
Pulse width of stimulation signal
为了增加鸽子生物机器人测试结果的可比较性,需要在所有测试中均采用刺激效果相当的单元刺激序列,所以在每一次户外测试之前都必须通过室内测试重新确定刺激参数。
2.2 户外测试
自由飞行的鸽子面对复杂的户外环境,为诱导出预期的盘旋动作往往需要多个单元刺激序列持续作用。但过长的刺激序列会对脑组织造成潜在损伤,一般控制在30 s以内为宜。为此,户外测试在逻辑调控流程中(见图1)设定可调用单元刺激序列的次数上限为8次。
户外飞行鸽子生物机器人的盘旋诱导共测试20组(见表1),包含2只鸽子(RP1和RP2)的左右向诱导盘旋各5次,总体成功率为90%,其中左向诱导成功率100%,右向诱导成功率80%。为避免过度刺激对鸽脑造成伤害的风险,逻辑调控流程中可调用单元刺激序列的数目上限设定为8次,并以8次以内刺激序列能够诱导出1次完整盘旋轨迹作为测试成功与否的判据标准。图7展示了表1中部分测试的飞行轨迹。成功的测试中,最少仅需施加1次单元刺激序列(见图7a),最多需要6次(见图7b);失败的测试中,施加8次单元刺激序列,仍未能实现盘旋诱导(见图7c)。
 图7
户外盘旋诱导测试
图7
户外盘旋诱导测试
a. 1次刺激诱导成功;b. 6次刺激诱导成功;c. 诱导失败
Figure7. Circling control during flying outdoora. success by 1 stimulation; b. success by 6 stimulations; c. failed case
2.3 飞行机动翼面形态测试
鸽子生物机器人的中央控制模块留有多种扩展接口,如接入微型轻量的图像采集装置,就可以在诱导自由飞行鸽子转弯机动的过程中,同步获取翅膀形态变化的细节(见图8)。图中展示了鸽子生物机器人的一段飞行轨迹(见图8a),以及在诱导转向开始前(见图8b)和转向中(见图8c)的翅膀翼面形态变化情况。空中转弯机动过程中,鸽子的外翼显著向后弯折,导致翼面的展向变形。
 图8
户外飞行诱导转向时的翼面变形
图8
户外飞行诱导转向时的翼面变形
a. 飞行轨迹;b. 转向前的翼面;c. 转向中的翼面
Figure8. Induced turning and wing morphinga. flight trajectory; b. before turning; c. during turning
2.4 集群演化干预效果测试
为探讨鸽子生物机器人对飞行集群的行为和演化是否会产生影响,初步测试了3只个体构成的小集群(1只鸽子生物机器人,2只自然鸽)。每只个体在鸽子集群中都有不同的等级[22, 26],即自由集群作出飞行方向选择时,个体是处于决定地位还是跟随地位。个体等级可由方向相关法[26]计算得到。选择不同等级的鸽子作为鸽子生物机器人,对集群演化的干预效果截然不同。当鸽子生物机器人处于相对高等级时(见图9a),它受控时的机动飞行对集群中其他个体影响显著;反之,当处于相对低等级时(见图9b),鸽子生物机器人受控时的机动飞行则明显受到集群中其他个体的影响。
 图9
飞行鸽群的内部协调
图9
飞行鸽群的内部协调
a. 高等级鸽子生物机器人的影响;b. 低等级鸽子生物机器人的影响
Figure9. Internal coordination in a flying pigeon flocka. robo-pigeon at high hierarchy; b. robo-pigeon at low hierarchy
3 讨论
3.1 影响户外测试效果的因素及本研究的局限
户外测试中的鸽子生物机器人运动调控效果明显不如室内,所需单元刺激序列的数目多、变化范围大,并且存在诱导失败的情况。分析影响户外测试效果的因素可能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户外自然环境复杂、不可预测,鸽子对视觉、气流等外界刺激的感受会与正常的脑电刺激响应相互叠加和影响,导致整体响应的迟钝和动作的不自然;其次,鸽子对长期重复的脑电刺激会产生一定的适应性,调控效果会由于适应性脱敏而逐渐减弱;最后,鸽子的个体存在差异性,对脑电刺激及外界环境的响应方式都会有所不同。
受制于野外生物活体实验数据获取的条件约束,本研究的样本量偏少,测试时间和空间也较为有限,存在不足之处。未来为了获得鸽子生物机器人更加稳定的性能和更加可靠的应用,后续研究需要从三方面加以完善:一是探索更丰富的功能脑区及神经核团,在中脑网状结构调控转弯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并拓展新的调控功能,如加减速、爬升下降等功能;二是获得更完备的实验设计和数据样本,长期积累单次/多次盘旋、S弯、上下坡等多种行为调控实验的数据样本;三是采用更宽泛的测试空间和外场环境,使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设计与测试更具普适性。
3.2 鸽子生物机器人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
尽管鸽子生物机器人在户外条件下尚无法达到精确的运动诱导和百分之百的诱导成功率,但其作为一种人工可控的生物工具,在自然环境下飞行动物个体或群体现象的科学研究中,已初步体现出应用价值。
一是研究鸽子机动飞行的翼面变形现象。动物飞行的机动性能远优于仿生飞行机器人,其机动过程中的翼面变形是仿生设计的要点之一。研究人员利用风洞等设备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简化的室内实验条件往往会忽略动物飞行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现象,而这些现象与机动性能的关系并不明确。可见在户外自然条件下,获取自由飞行动物的实验数据十分必要[27-28],但如何高效率高质量地获取各类飞行机动数据,是实践操作的难点所在。如果利用鸽子生物机器人的飞行调控功能,并辅以各类功能载荷,则有望解决上述难题。例如,配备了微型轻量的图像采集装置的鸽子生物机器人(见图8),可以同步获取其自由飞行机动时的运动轨迹、翅膀形态变化细节等各类实验数据,这对飞行力学的研究和仿生飞行机器的设计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二是研究鸽子集群飞行的内部协调机制。随着无人机技术的日益成熟,军民均具应用潜力的无人机集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个体间如何协调以发挥出更大的群体优势,是无人机集群研究的难点和热点。而在自然界中,生物的大规模集群现象普遍存在,鸟群作为空中集群的典型代表,其集群飞行的复杂行为及底层的协调机制广受关注。但是,由于自由飞行鸟群的运动具有很大随意性且难于干预,目前对鸟群运动的研究大多基于长期观察和数学建模,效率不高,不易抓住鸟群个体间协调的本质。如何在自由飞行鸟群中加入人工可控因素,以提高研究的系统性和效率,是鸽子集群飞行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29-30]。如果把携带神经调控代码的鸽子生物机器人作为鸽群的一员,则可以通过人工诱导鸽子生物机器人飞行机动的方式,在鸽群中加入人工可控因素,有望解决上述难题。例如,本研究在三只个体构成的小型家鸽集群测试中(见图9),处于相对高等级的鸽子生物机器人可以显著影响集群的飞行方向选择,通过对鸽子生物机器人的盘旋动作的诱导,实现了对整个集群飞行行为的操控。这类研究可以扩展到更大的集群,逐步揭示集群的复杂性,还可对无人机集群的协调算法设计有所启示。
4 结论
本研究依托神经调控原理和脑机接口技术,提出了一种生物机器人的逻辑调控方法,设计制作了控制系统的软硬件,实现了可在户外自由飞行条件下运动调控的鸽子生物机器人。控制系统尺寸小(30 mm × 30 mm × 12 mm),重量轻(含电源重11.8 g),续航时间长(约为4 h),能够满足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背载及户外工作要求。以机器取代人工对鸽子运动状态的监测,实现逻辑调控闭环,突破了鸽子生物机器人工作半径的制约,适用于户外广阔的空间。脑电刺激信号仿照神经细胞动作电位设计并以间歇激活方式工作,可减轻对鸽子脑组织造成的损伤。在户外自由飞行条件下,鸽子生物机器人展示了转向及盘旋运动的可诱导性,并在鸽子机动飞行的翼面变形现象、集群飞行的内部协调机制等研究方向体现出应用价值。
致谢:作者感谢蔡雷、吴锦、李俊杰、朱志坚等在持续优化脑接接口和神经调控参数的工作中做出的贡献。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王浩负责实验设计、数据分析、论文写作,王绍康、邱兆成、张琦、许帅负责实验开展、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伦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批文编号:JSNUAA20180056)。
引言
生物机器人具有生物和机器的双重属性,是把生物有机体作为载体的特种机器人,是人类通过控制技术施加干预信号调控生物行为从而实现人类操控的生物[1-2]。可见,生物机器人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充分利用自然界动物在陆上[3-6]、水下[7-9]、空中[10-12]的运动能力。然而,受制于遥控遥测手段和通讯距离的限制[13],大多数生物机器人的受控范围局限于室内或室外几百米的半径内,这极大地限制了生物机器人的运动潜能和应用潜力。特别是对以归巢本能和长距离飞行为特点的鸽子生物机器人[14-16]而言,实现其户外飞行的视距外运动调控尤为重要。舍弃实时通讯,在远端控制系统直接编程控制指令,以预设条件触发固定的脑电刺激信号,为解决户外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视距外调控提供了思路[17]。这种预编程调控模式解决了鸽子生物机器人在操作人员视距外运动时如何产生控制指令的问题,但还缺乏反馈,未形成控制闭环。
另一方面,随着生物机器人技术的日趋成熟,发掘这项技术的应用出口已提上日程。除了侦察与救援这一热门应用方向[18-19],把生物机器人作为人工可控的科学工具,用于动物个体及集群的运动、协调、交互等各类行为机制及仿生应用的研究[20-22],也逐渐受到重视。
鸽子生物机器人已经具有了可靠的微电刺激~运动响应范式,在80 Hz正负双相电压刺激脉冲的作用下,通过调节刺激脉冲占空比、脉冲序列的长短及周期性间隔,可以实现转弯、盘旋等多种飞行动作的控制[17, 22],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本文针对鸽子生物机器人发展和应用的需求,采用逻辑调控思路,依托神经调控原理和脑机接口技术,设计了一种可实现户外飞行闭环控制的鸽子生物机器人,并展示了该机器人在扑翼飞行和集群协调等研究领域的应用。鸽子背载的控制系统中预设机动任务,如在特定区域或时刻开始转向或盘旋;系统借助北斗导航模块对飞行轨迹实时监测,并解算当前飞行状态;依据调控逻辑触发控制指令,发送脑电刺激信号;判断机动任务的执行情况,并形成下一步指令。
1 闭环控制系统
1.1 系统逻辑
自然界鸽子飞行能力较强,具体表现在:飞行距离远,一般在十公里以上[17];飞行速度快,平均时速约60 km/h[17],短时间内爆发速度可达100 km/h;巡航飞行高度约为150 m,同时个体负载能力有限。鸽子飞行的这些特点限制了现有生物机器人通讯技术[13]在鸽子生物机器人上的应用,尤其在户外远距离场景下,无法构成地面端人工监测中心和远端鸽子生物机器人的控制闭环。本文提出,在生物机器人背载设备的神经刺激功能之上,增加运动监测功能,以在体机器监测替代远端人工监测,用逻辑算法实现生物机器人的控制闭环。运动监测功能的实现依托全球卫星定位导航技术[23],选用外形小巧、定位精度更优的国产北斗模块[24]。模块设置了最高时间分辨率(5 Hz),以满足快速飞行采样的要求。鸽子生物机器人闭环控制系统的逻辑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鸽子生物机器人闭环控制逻辑流程
Figure1.
Logic flow of the closed loop control in a pigeon-robot
图1
鸽子生物机器人闭环控制逻辑流程
Figure1.
Logic flow of the closed loop control in a pigeon-robot
1.2 软硬件设计
我们设计的鸽子生物机器人的整体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其中,在体控制系统包括中央控制模块、运动监测模块、神经刺激模块、数据存储模块;脑机接口是控制系统与鸽脑的连接;马甲或背贴用于控制系统的穿戴或背载。图中箭头表示数据流向,实线段表示物理连接。中央控制模块主要由嵌入式系统中央处理器STM32F103RBT6和电源管理芯片RT9193、TC7660EOA组成;运动监测模块由北斗导航单元ATGM336H和无源陶瓷天线组成;神经刺激模块由中控的GPIO与运算放大器MC33202组成;脑机接口结合鸽子颅骨特性设计[25]。
 图2
鸽子生物机器人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ure2.
System diagram of a pigeon-robot
图2
鸽子生物机器人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ure2.
System diagram of a pigeon-robot
1.2.1 系统硬件
系统硬件的电路原理如图3所示。中央控制模块的核心是STM32F103RBT6芯片(意法半导体),工作时钟最高为72 MHz。在KEIL开发环境(Keil Software,美国)下编译成功的控制程序贮存在芯片存储器中。当系统上电后,芯片根据设定的时序依次在存储器中调用程序,设置相应的数据寄存器,并配置输入输出端口。控制程序从外周设备读取数据,通过运算模块对数据进行代数及逻辑运算,并依据运算结果形成输出指令,产生下一步操作。中央控制模块由一片锂电池(3.7 V,400 mAh)供电,可以持续供电4 h左右。电源管理包括稳压电路、负压转换电路、抗干扰及过压保护电路。稳压电路选用RT9193,产生3.3 V恒压为系统各模块供电;负压转换电路选用TC7660EOA,为双相脑电刺激信号提供负压;抗干扰电路采用滤波方式以减轻来自电源的耦合干扰,过压保护电路避免电路中突然的过压烧坏元器件。另外,中央控制模块预留接口,用于功能扩充。
 图3
控制系统电路原理图
Figure3.
The circuit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trol system
图3
控制系统电路原理图
Figure3.
The circuit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trol system
运动监测模块采用商用北斗模组ATGM336H(中科微电子,中国),其灵敏度高,支持BDS、GPS和GLONASS三种卫星导航系统的单系统定位以及任意组合的多系统联合定位。模组的配置可在PC端使用GNSSToolKit工具实现,设置上限采样率(5 Hz)以匹配鸽子的飞行速度,同时设定UART接口RXD/TXD的波特率为15.2 kBit/s;为减少数据传输量,按NMEA-0183协议仅选择$GNRMC帧信息,输出仅包含经度、纬度、高度及时间信息的BDS定位数据。运动监测模块与中央控制模块通过SPI协议进行数据传送,电气上直接与PA9(TXD)和PA10(RXD)连接。
神经刺激模块由中央控制模块的GPIO输出与运算放大器MC33202共同组成。主控程序产生脉宽可调的PWM信号,其中一路不作分压处理,另一路通过电阻分压降低信号幅值,两路信号经由运算放大器MC33202进行减法运算,可以产生幅值与脉宽灵活多变的双相脑电刺激信号。
数据存储模块由TF卡及其驱动电路组成。TF卡存储容量可达8 GB,可记录实验过程中的各类数据。数据存储模块通过SPI总线与中央控制模块连接,以DMA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脑机接口在文献[25]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通过脑机接口植入两根刺激电极和一根参考电极。刺激电极的目标靶点位于鸽子中脑网状结构(formation reticularis medialis mesencephali,FRM)的左右双侧,即以耳杆连线中点为空间坐标系原点,矢向取3.0~3.6 mm,冠向取1.0~2.5 mm,纵向取4.0~6.5 mm;参考电极置于头部皮下的一侧颅骨上。
鸽子生物机器人控制系统(见图4a)的外形尺寸为30 mm×30 mm×12 mm,含电池重量为11.8 g,其背载方式有背贴式和马甲式两种。背贴式即在鸽子左右翅根之间的背部区域、背载设备的底面,分别粘贴尼龙搭扣的两部分,该方式背载、脱离方便,适用于一体化的背载设备(见图4b);马甲式即用弹性布料量体裁制组合式马甲(见图4c),可套头穿戴至胸腹部,在马甲上可以穿引导线用于电气连接,适用于分布式的背载设备(见图4d)。
 图4
硬件实物图
图4
硬件实物图
a. 控制系统;b. 背贴式背载;c. 马甲;d. 马甲式背载 (彩图)
Figure4. Photos of pigeon-robotsa. control system; b. wearing by Velcro; c. pigeon vest; d. wearing by vest
1.2.2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在KEIL开发平台编辑、编译和调试,确保工作流程(见图1)的执行。软件除了驱动系统硬件、协调外周模块等次要功能外,主要功能是实现鸽子生物机器人的逻辑调控:一是利用运动监测模块硬件获取的实时坐标数据分析飞行调控任务执行情况,二是结合神经刺激模块硬件构造双相脑电刺激信号。
运动监测模块实时获取当前地理经纬度坐标,并依据WGS-84系统规则把经纬度坐标转换为笛卡尔坐标(以鸽舍为坐标原点),以当前时刻坐标与上一时刻坐标的矢量差解算当前的飞行速度与方向。当飞行调控任务启动后,令脑电刺激开始前的飞行方向为参考方向;之后每施加一次单元刺激序列(见后文定义),进行一次飞行方向解算,并与参考方向比较获得飞行偏角;以飞行偏角的数值判定任务是否达到预期。对于转向任务,设定具体的预期偏角;对于盘旋任务,以飞行偏角超过±270°(+代表左盘旋,–代表右盘旋)为判据,此后即使没有后续刺激,鸽子也会本能地继续转向,以回归刺激前的飞行方向。
神经刺激模块输出的单元刺激序列为一时长4 s的脉冲串信号,前2 s为刺激脉冲串,后2 s为零电平,以避免持续电刺激对脑组织造成损伤。刺激脉冲串的频率为80 Hz(周期12.5 ms,由系统72 M主频、1 000分频、900重装载值决定),刺激波形由中控GPIO产生的两路PWM波经由运算放大器减法合成,产生正负幅值比例、正负脉宽比例均可调的双相刺激信号(见图5a)。单个刺激脉冲的波形仿照神经细胞动作电位设计。神经细胞动作电位(见图5b)包含一个细胞膜电位快速由负电位上升至正电位然后回落的过程。由负升正段由去极化(图5b中b-c段)和反极化/超射(图5b中c-d段)构成,过程陡峭,此时膜内的负电位迅速消失并继而变为正电位,膜内外电位差快速升高;回落段由复极化(图5b中d-e段)构成,过程相对较缓,膜内外电位差逐步回落,并最终恢复至静息负电位。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脑电刺激信号按照上述膜电位生理过程设计,在刺激目标靶区用较短的时间施加较大的负电压(–3.3 V)以注入负电荷,然后用两倍的时间施加较小正电压(+1.65 V),形成模拟动作电位的刺激信号(见图5c)。在软件中调整PWM的占空比和脉冲幅值,使PWM1的幅值是PWM2的一半,而脉宽是其两倍,且满足相位关系,即可实现单刺激脉冲的合成。单元刺激序列则是由160个单刺激脉冲组成的连续刺激脉冲串。
 图5
脑电刺激信号设计
图5
脑电刺激信号设计
a. 双相刺激信号合成;b. 神经细胞动作电位;c. 示波器显示的单个刺激脉冲
Figure5. Design of the brain stimulation signala. synthesis of biphasic signals; b. action potential of nerve cell; c. stimulation pulse in oscilloscope
2 动物实验和结果
动物实验所用的鸽子,在当地信鸽协会的指导和监督下,由课题组自主饲养和繁育。实验选用两只月龄6个月以上的成年鸽,体重范围在400~500 g之间。经外科手术植入控制电极并安装脑机接口的鸽子生物机器人在恢复3~5天后,进行室内和户外运动调控测试。室内测试的目的是检验调控的有效性,并确定户外测试所需的脑电刺激参数。户外测试在合适的天气条件(晴天、微风)下进行。鸽子生物机器人于10 km外独自归巢,约10 min的飞行行程。为避免起飞和降落阶段的自主飞行机动影响,逻辑调控在行程中段进行,时间窗口有限,仅调控左、右盘旋各一次。实验共进行5次,分别在5个上午进行。在室内和户外测试确认了鸽子生物机器人飞行调控有效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测试了鸽子生物机器人的两类应用能力:一是同步获取自身机动飞行轨迹和翼面形态的能力,二是干预影响所属集群决策和演化的能力。前者通过单只鸽子生物机器人展示;后者由1只鸽子生物机器人和2只自然鸽构成的集群展示,其中自然鸽的月龄和体重与鸽子生物机器人相当。
2.1 室内测试
室内测试鸽子生物机器人在1次单元刺激序列作用下身体转向的角度,并在调控有效的前提下确定脑电刺激脉冲参数。刺激脉冲的脉冲频率及正负相电压幅值恒定不变,可变参数仅为刺激脉宽P。由于正负相脉宽比例恒定,以负相脉宽定义参数P,取值范围在0.014~4.167 ms,变化步长近似为0.014 ms;正相脉宽是负相的2倍。测试以两分钟为间隔,逐步增加刺激脉冲的P值,直到该脉宽的单元刺激序列能够诱导出鸽子原地转向360°的动作。即,确定诱导鸽子原地转向一周所需的最小脉宽值,为后续户外测试所用。对左右脑目标靶区的刺激参数采用相同的方式确定。
全部室内测试均实现了鸽子生物机器人原地360°转向诱导,所需刺激脉宽如图6所示。可见,不同个体、不同脑区的刺激脉宽有较大差异,这是由动物间的个体差异以及电极植入位点的定位误差所致。另外,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为实现相同诱导动作所需的刺激脉宽P也在逐渐增大。生物组织对侵入的异物会产生自然的排异反应,从异物尖端开始逐渐产生包裹层。随着电极尖端触点周围包裹层的日益增厚,其组织阻抗增大、电传导性变差,同等强度刺激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为达到相同的刺激效果,需要增大刺激强度。一般而言,植入刺激电极后的两周至一个月内,是鸽子生物机器人最佳测试时间。
 图6
刺激脉宽
Figure6.
Pulse width of stimulation signal
图6
刺激脉宽
Figure6.
Pulse width of stimulation signal
为了增加鸽子生物机器人测试结果的可比较性,需要在所有测试中均采用刺激效果相当的单元刺激序列,所以在每一次户外测试之前都必须通过室内测试重新确定刺激参数。
2.2 户外测试
自由飞行的鸽子面对复杂的户外环境,为诱导出预期的盘旋动作往往需要多个单元刺激序列持续作用。但过长的刺激序列会对脑组织造成潜在损伤,一般控制在30 s以内为宜。为此,户外测试在逻辑调控流程中(见图1)设定可调用单元刺激序列的次数上限为8次。
户外飞行鸽子生物机器人的盘旋诱导共测试20组(见表1),包含2只鸽子(RP1和RP2)的左右向诱导盘旋各5次,总体成功率为90%,其中左向诱导成功率100%,右向诱导成功率80%。为避免过度刺激对鸽脑造成伤害的风险,逻辑调控流程中可调用单元刺激序列的数目上限设定为8次,并以8次以内刺激序列能够诱导出1次完整盘旋轨迹作为测试成功与否的判据标准。图7展示了表1中部分测试的飞行轨迹。成功的测试中,最少仅需施加1次单元刺激序列(见图7a),最多需要6次(见图7b);失败的测试中,施加8次单元刺激序列,仍未能实现盘旋诱导(见图7c)。
 图7
户外盘旋诱导测试
图7
户外盘旋诱导测试
a. 1次刺激诱导成功;b. 6次刺激诱导成功;c. 诱导失败
Figure7. Circling control during flying outdoora. success by 1 stimulation; b. success by 6 stimulations; c. failed case
2.3 飞行机动翼面形态测试
鸽子生物机器人的中央控制模块留有多种扩展接口,如接入微型轻量的图像采集装置,就可以在诱导自由飞行鸽子转弯机动的过程中,同步获取翅膀形态变化的细节(见图8)。图中展示了鸽子生物机器人的一段飞行轨迹(见图8a),以及在诱导转向开始前(见图8b)和转向中(见图8c)的翅膀翼面形态变化情况。空中转弯机动过程中,鸽子的外翼显著向后弯折,导致翼面的展向变形。
 图8
户外飞行诱导转向时的翼面变形
图8
户外飞行诱导转向时的翼面变形
a. 飞行轨迹;b. 转向前的翼面;c. 转向中的翼面
Figure8. Induced turning and wing morphinga. flight trajectory; b. before turning; c. during turning
2.4 集群演化干预效果测试
为探讨鸽子生物机器人对飞行集群的行为和演化是否会产生影响,初步测试了3只个体构成的小集群(1只鸽子生物机器人,2只自然鸽)。每只个体在鸽子集群中都有不同的等级[22, 26],即自由集群作出飞行方向选择时,个体是处于决定地位还是跟随地位。个体等级可由方向相关法[26]计算得到。选择不同等级的鸽子作为鸽子生物机器人,对集群演化的干预效果截然不同。当鸽子生物机器人处于相对高等级时(见图9a),它受控时的机动飞行对集群中其他个体影响显著;反之,当处于相对低等级时(见图9b),鸽子生物机器人受控时的机动飞行则明显受到集群中其他个体的影响。
 图9
飞行鸽群的内部协调
图9
飞行鸽群的内部协调
a. 高等级鸽子生物机器人的影响;b. 低等级鸽子生物机器人的影响
Figure9. Internal coordination in a flying pigeon flocka. robo-pigeon at high hierarchy; b. robo-pigeon at low hierarchy
3 讨论
3.1 影响户外测试效果的因素及本研究的局限
户外测试中的鸽子生物机器人运动调控效果明显不如室内,所需单元刺激序列的数目多、变化范围大,并且存在诱导失败的情况。分析影响户外测试效果的因素可能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户外自然环境复杂、不可预测,鸽子对视觉、气流等外界刺激的感受会与正常的脑电刺激响应相互叠加和影响,导致整体响应的迟钝和动作的不自然;其次,鸽子对长期重复的脑电刺激会产生一定的适应性,调控效果会由于适应性脱敏而逐渐减弱;最后,鸽子的个体存在差异性,对脑电刺激及外界环境的响应方式都会有所不同。
受制于野外生物活体实验数据获取的条件约束,本研究的样本量偏少,测试时间和空间也较为有限,存在不足之处。未来为了获得鸽子生物机器人更加稳定的性能和更加可靠的应用,后续研究需要从三方面加以完善:一是探索更丰富的功能脑区及神经核团,在中脑网状结构调控转弯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并拓展新的调控功能,如加减速、爬升下降等功能;二是获得更完备的实验设计和数据样本,长期积累单次/多次盘旋、S弯、上下坡等多种行为调控实验的数据样本;三是采用更宽泛的测试空间和外场环境,使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设计与测试更具普适性。
3.2 鸽子生物机器人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
尽管鸽子生物机器人在户外条件下尚无法达到精确的运动诱导和百分之百的诱导成功率,但其作为一种人工可控的生物工具,在自然环境下飞行动物个体或群体现象的科学研究中,已初步体现出应用价值。
一是研究鸽子机动飞行的翼面变形现象。动物飞行的机动性能远优于仿生飞行机器人,其机动过程中的翼面变形是仿生设计的要点之一。研究人员利用风洞等设备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简化的室内实验条件往往会忽略动物飞行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现象,而这些现象与机动性能的关系并不明确。可见在户外自然条件下,获取自由飞行动物的实验数据十分必要[27-28],但如何高效率高质量地获取各类飞行机动数据,是实践操作的难点所在。如果利用鸽子生物机器人的飞行调控功能,并辅以各类功能载荷,则有望解决上述难题。例如,配备了微型轻量的图像采集装置的鸽子生物机器人(见图8),可以同步获取其自由飞行机动时的运动轨迹、翅膀形态变化细节等各类实验数据,这对飞行力学的研究和仿生飞行机器的设计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二是研究鸽子集群飞行的内部协调机制。随着无人机技术的日益成熟,军民均具应用潜力的无人机集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个体间如何协调以发挥出更大的群体优势,是无人机集群研究的难点和热点。而在自然界中,生物的大规模集群现象普遍存在,鸟群作为空中集群的典型代表,其集群飞行的复杂行为及底层的协调机制广受关注。但是,由于自由飞行鸟群的运动具有很大随意性且难于干预,目前对鸟群运动的研究大多基于长期观察和数学建模,效率不高,不易抓住鸟群个体间协调的本质。如何在自由飞行鸟群中加入人工可控因素,以提高研究的系统性和效率,是鸽子集群飞行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29-30]。如果把携带神经调控代码的鸽子生物机器人作为鸽群的一员,则可以通过人工诱导鸽子生物机器人飞行机动的方式,在鸽群中加入人工可控因素,有望解决上述难题。例如,本研究在三只个体构成的小型家鸽集群测试中(见图9),处于相对高等级的鸽子生物机器人可以显著影响集群的飞行方向选择,通过对鸽子生物机器人的盘旋动作的诱导,实现了对整个集群飞行行为的操控。这类研究可以扩展到更大的集群,逐步揭示集群的复杂性,还可对无人机集群的协调算法设计有所启示。
4 结论
本研究依托神经调控原理和脑机接口技术,提出了一种生物机器人的逻辑调控方法,设计制作了控制系统的软硬件,实现了可在户外自由飞行条件下运动调控的鸽子生物机器人。控制系统尺寸小(30 mm × 30 mm × 12 mm),重量轻(含电源重11.8 g),续航时间长(约为4 h),能够满足鸽子生物机器人的背载及户外工作要求。以机器取代人工对鸽子运动状态的监测,实现逻辑调控闭环,突破了鸽子生物机器人工作半径的制约,适用于户外广阔的空间。脑电刺激信号仿照神经细胞动作电位设计并以间歇激活方式工作,可减轻对鸽子脑组织造成的损伤。在户外自由飞行条件下,鸽子生物机器人展示了转向及盘旋运动的可诱导性,并在鸽子机动飞行的翼面变形现象、集群飞行的内部协调机制等研究方向体现出应用价值。
致谢:作者感谢蔡雷、吴锦、李俊杰、朱志坚等在持续优化脑接接口和神经调控参数的工作中做出的贡献。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王浩负责实验设计、数据分析、论文写作,王绍康、邱兆成、张琦、许帅负责实验开展、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伦理声明:本研究通过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批文编号:JSNUAA2018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