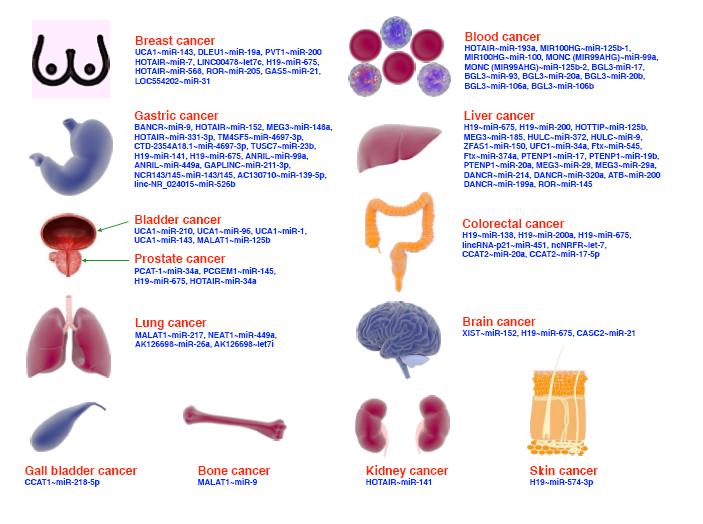虽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作为一种支持呼吸或心脏功能的手段就已存在,但其早期应用仍受到并发症发生率较高的困扰。外周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eno-arteri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V-A ECMO)的应用会引起左室舒张末期压力升高、肺水肿、左室扩张、室性心律失常、冠状动脉低灌注、心肌缺血、心内血栓形成、多器官功能障碍等严重并发症,需要行机械性左心减压来治疗上述相关并发症。本文回顾了心源性休克患者外周 V-A ECMO 支持下左心减压的相关问题。
引用本文: 闫阳波, 干昌平. 心源性休克患者外周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支持下左心减压的相关问题.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1, 28(9): 1114-1118. doi: 10.7507/1007-4848.202011090 复制
1 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
1.1 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的置管方式及适应证
目前,基于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的临床适应证,其置管方式可分为两大类,即静脉-静脉(V-V ECMO)型和静脉-动脉(V-A ECMO)型。V-V ECMO 的基本置管方式为经股静脉和颈静脉两个位置分别置管,在该种置管方式下,血液自股静脉引出体外,氧合后经颈静脉回输体内;近年来也有经“Y”形双极管安置导管的颈静脉单位置的置管方式。而 V-A ECMO 的最常用置管方式外周型,即置管位置为股静脉和股动脉两个位置,血液自股静脉引出,氧合后经股动脉回输入体内;但在这种置管方式下,会出现所谓的“对冲平面”,影响脑及冠状动脉的血供,因此,也有在外周型置管方式的基础上,在股动脉导管处接一“Y”形双极导管,自股动脉导管处另连导管至颈内静脉,以使氧合血可直接回到心脏并得以滋养冠状动脉及脑,该种置管方式称为 V-A-V ECMO(venoarterial-venous ECMO)[1]。因为经外周股动、静脉插管安置 V-A ECMO 操作简便,实施迅速,出血风险小,在 ICU 床旁便可完成,是目前临床上最常采用的体外生命支持模式。
总的来说,V-A ECMO 主要用于为各种病因所致心功能障碍提供短期(几天至几周)的循环支持和/或呼吸支持。ECMO 本身并不能治疗各种原发疾病,但可以支持心肺功能及改善全身脏器灌注,而且可以帮助心脏得到休息,为下一步决策争取时间,为器官功能恢复赢得机会,为心跳骤停患者评估神经系统预后,为需要心脏移植或者长时间机械循环辅助重度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提供过渡性治疗。其主要适应证有:(1)各种病因所致的心源性休克,也包括心脏术后或原发性移植物衰竭所致的心源性休克;(2)心脏骤停时与心肺复苏的联用(extracorporeal cardiopulmonary rescuscitation,ECPR);(3)难治性的室性心律失常;(4)暴发性心肌炎;(5)肺栓塞;(6)心脏移植或左室辅助装置时的过渡性治疗等[1-2]。目前 V-A EMCO 最主要的适应证仍是各种原因所致的心源性休克。急性心力衰竭是指短时间内由心脏泵功能减弱所引发的循环功能障碍,广义上也包含由此引发的多器官功能不全的临床状态。心源性休克是急性心力衰竭最为危重的表现形式,当并发急性心肌梗死时,死亡率可高达 50%~60%[3]。临床上心源性休克的定义为:收缩压≤90 mm Hg,心脏指数(CI)<2.0 L/(min·m2),左室舒张末期压力(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pressure,LVEDP)>16 mm Hg,出现组织低灌注的临床表现,伴随或不伴随乳酸升高。心源性休克期间,不仅心脏功能会继续恶化,同时由于心输出量急剧下降,全身组织器官低灌注,还有约 32% 的患者继发心脏以外的多器官功能障碍,严重影响预后[4-5]。体外生命支持这一概念及相关技术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已经在多项研究中被证实能够改善急性心力衰竭状态下难治性心跳骤停患者的死亡率和神经系统预后。心外科术后并发心源性休克的患者,使用体外生命支持可使其生存率增加约 1.5 倍[6]。体外生命支持的种类很多,包括完整的心肺转流(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ECMO 以及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等。其中 V-A ECMO 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体外生命支持类型,也是美国心脏协会(AHA)推荐用于治疗急性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的首选[7]。也有文献[8-9]报道,V-A ECMO 可应用于感染性休克治疗过程的生命支持,但相比于心源性休克,V-A ECMO 在感染性休克的支持效果远比不上心源性休克。
1.2 外周 V-A ECMO 中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及其对器官功能的影响
在最常用的外周股动、静脉置管的方式中,血液自股静脉引出体外,氧合后的血液经股动脉-髂动脉-腹主动脉-胸主动脉的血流方向进入体内,这与心脏射血方向(左室-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腹主动脉)截然相反,从而抵消一部分心脏射血的力量,形成所谓的“对冲平面”[10-11],随着左心残余功能及 ECMO 流量的不同,“对冲平面”可以出现在主动脉的任一位置。这带来的主要表现为:由于心脏射血的力量被部分抵消,左室后负荷增加,LVEDP 会升高[12],有研究[13]表明,在心源性休克状态下,ECMO 的流量分别为 1.5 L/min、3.0 L/min、4.5 L/min 时描记出的压力-容积曲线表明,LVEDP 随着 ECMO 的流量增大会逐渐升高,且 LVEDP 的变化比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LVEDV)的变化更加明显。LVEDP 的升高将进一步引发肺水肿、左室扩张、室性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心内血栓形成、多器官功能障碍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14-16]。有研究[17]发现,当狗的左房压高于 24 mm Hg 维持 30 min,可使肺水肿呈指数性增加,维持 3 h 则没有动物能够存活。可见,持续升高的左房压还将引起级联反应式的多器官功能障碍,不可逆肺水肿甚至呼吸窘迫综合征等心外器官损害,同样严重危害预后。
2 左心减压
2.1 左心减压的必要性
在外周股动、静脉置管的方式下,LVEDP 的升高会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因此,在 V-A ECMO 中,如何在充分维护脏器灌注的同时,降低左室后负荷,保证心肌充分休息和促进其恢复,避免严重心脏及心外脏器功能障碍的发生,成为 ECMO 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有研究[18]表明,适度下调 ECMO 流量、增加强心药物剂量促进心脏射血、减少缩血管药物使用等方式虽然可以不同程度地降低左室后负荷,然而这些治疗手段不但减低左室后负荷的效能极其有限,而且可能以牺牲 ECMO 效能、降低组织灌注和氧供以及增加心肌氧耗作为代价,对极度衰竭的左心来说,可能对其恢复是不利的[19]。因此近年来,更加积极的机械性左心减压手段逐渐应用于临床,包括: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房间隔造口、房间隔支架、肺动脉、左心房及左心室插管直接减压,经皮跨主动脉瓣左室减压和左心辅助装置等,不同程度地改善了患者的预后。有研究[20-21]证实,联合 ECMO 和 Impella 5.0 能够通过更充分的左心减压加快 ECMO 的成功撤离;心肌活检显示充分左心减压能够帮助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心肌恢复;早期左心减压,更能够为后续的介入诊断治疗提供更为稳定的患者状态、减少强心药物的使用、改善心肌灌注、减少心肌坏死。而其它机械性减压手段如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房间隔造口、经皮跨主动脉瓣左室减压和左心辅助装置等手段的应用,也使得 30 d 死亡率降低、血管活性药物剂量降低、ECMO 及呼吸机脱机率升高、ICU 及住院时间缩短以及心脏移植或人工心脏移植率增高等[12, 22-26]。
尽管越来越多的观察性研究肯定了在急性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状态下行 V-A ECMO 支持的患者中左心减压对某些临床指标的改善作用,但多数研究也证实其对改善器官功能以及死亡率等终点指标并无益处。Russo 等[27]的研究表明,V-A ECMO 联用左心减压时全因死亡率比不联用左心减压的患者更低(54% vs. 65%),虽然减压组溶血发生率更高,但出血、肢体缺血、肾脏替代治疗、多器官衰竭以及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在减压组和不减压组的发生率相近。同时,额外的减压,特别是外科性操作,不仅大大增加危重患者出血和感染的风险,增加 ECMO 管路的复杂程度,还大大增加治疗费用[28-31]。 因此,在考虑是否行左心减压时,筛选合适的患者可能会减轻并发症,对于心功能更具恢复能力的患者,需要更加积极的减压。Camboni 等[32]认为,在评估心功能恢复的可能性时,需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基础心脏病,急性且可治疗的急性心脏病(如心肌炎、再通的急性心肌梗死)与终末期的慢性心力衰竭相比,心功能更容易恢复;(2)支持的有效性和终末器官对氧气反应性,持续低下的静脉血氧饱和度、长期持续升高的乳酸水平和持续性酸中毒的患者具有较小的恢复潜力,而动脉血气立即恢复正常的患者则具有较大的恢复潜力;(3)超声心动图有助于识别心功能的恢复潜力,在使用 ECMO 最初的 24 h 内心室功能改善的患者比心室高度扩张、无射血、主动脉瓣关闭和心室淤滞的患者具有更大的恢复潜力。
2.2 左心减压的手段
目前,机械性左心减压的手段也已趋向于多元化。按创伤大小,则分为外科手段和经皮微创入路。外科手段通常为经胸骨正中切口、胸骨旁小切口、剑突下切口及经膈肌等入路,在右上肺静脉、肺动脉、左心耳及左心尖等部位置入引流管行左心减压;而经皮途径则经股动、静脉穿刺入路后,置入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mpella 等装置,或行房间隔造口术及经皮超声引导心房分流器植入术等手段行左心减压[23, 33-35]。但最初实施 ECMO 时绝大多数是因在床旁完成而没有开胸,或者心脏术后基于需要左心减压的考虑而延迟关胸,其难度和代价都很高,所以在外周 V-A ECMO 的情况下,可能会更倾向于介入的方法进行左心减压。
2.3 左心减压的时机
目前,减压时机和指征差别巨大,对于左心减压的时机,成人和儿童也不尽相同。
对于成人而言,由于外周 V-A ECMO 固有的血流动力学的缺陷,在其使用过程中,会引起 LVEDP 升高,除了因压力逆传引起肺水肿、急性肺损伤等并发症,也可导致左室扩张[36]。但一般认为成人对升高的 LVEDP 的耐受性较好,因此,对于 V-A ECMO 所致的左室扩张,通过适度下调 ECMO 流量、正性肌力药及扩血管药物等血管活性药物的合理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LVEDP,这时,轻度升高的 LVEDP 对于成人而言是可以接受的[18],考虑到前述的左心减压的操作会带来出血、感染等并发症,成人左心减压往往采取较保守的策略,只有在极严重的左室扩张时,才会考虑行左心减压。 Truby 等[37]将左室扩张按程度分为 3 类,分别为:(1)亚临床左室扩张(subclinical LVD,LVD+): V-A ECMO 支持后的前 2 h 内,胸部 X 线片显示肺水肿和肺动脉舒张压>25 mm Hg;(2)左室扩张(LVD++):由于肺水肿、室性心律不齐或左室内血液明显瘀滞,需要在 V-A ECMO 启动后立即进行中心减压;(3)无左室扩张(LVD–):不满足上述 LVD+的诊断标准,也不需要立即减压者。而 LVD++和 LVD+需要考虑减压,LVD–者则暂时不需要行左心减压。但 Cheng 等[38]发现在 V-A ECMO 治疗过程中,由于肺血管灌注不足,肺静脉损伤的严重程度可能会被低估,从而导致胸部 X 线片上肺水肿的表现不明显,在肺血管血流恢复后,肺水肿的影像学表现会显现出来,这提示我们,按照 Truby 等的减压标准,可能会因未能及时从胸部 X 线片上识别肺水肿而延误一部分患者的治疗。
相较于成人而言,儿童对左室扩张的耐受性更差,更易因此而出现心脏结构性损伤。因此,儿童左心减压更为积极。有些医学中心常规在 V-A ECMO 支持治疗起始时[18],最晚不超过 12 h 内联用左心减压:在 Kotani 等[39]的研究中,178 例患者使用 V-A ECMO 支持治疗,有 23 例患者经历了左房减压:其中 16 例(70%)患者在 ECMO 启动时经历了左房减压,并且在 ECMO 启动后 12 h 内所有 23 例患者经历了左房减压,结果为 ECMO 支持时间为(5.9±4.5)d,16 例(70%)患者成功脱机,ICU 生存率和医院生存率分别达到 57%和52%。Zampi 等[40]参与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通过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确定 ECMO 转机后 18 h 为早期减压与晚期减压的临界点,早期减压(V-A ECMO 支持治疗后 18 h 内行左房减压)与晚期减压(V-A ECMO 支持治疗 18 h 后行减压治疗)相比,早期减压组机械通气支持时间短于晚期减压[早期减压 10(7,15)d vs. 晚期减压 17(10,29)d,P=0.01]。Sandrio 等[41]观察到在 8 例心脏术后或心脏病所致的低心排血量的儿童患者,在机械生命支持的同时予以左室减压后,脱机率高,平均支持时间 6 d,期间未观察到心内血栓或栓塞性卒中,也未出现因颅内出血而导致体外生命支持期间和之后出现神经功能障碍。这些研究都证实了积极的左心减压可以改善患儿的预后。但是也有相反的研究结果表明,减压对于儿童未带来明显的益处:Alghanem 等[42]发现,减压虽然成功降低了平均左房压力,但减压组和对照组院内死亡率相近(29% vs. 38%,P=0.513),且减压组住院时间更长。
目前在临床上,左心减压多为在外周 V-A ECMO 并发症的治疗性手段。我们知道,在外周 V-A ECMO 治疗过程中,LVEDP 升高会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预后,那么从 ECMO 治疗起始时就积极地应用左心减压,打断上述压力逆传的过程,能否改善患者的预后呢? Kotani 等[39]及 Zampi 等[40]的研究均证实,ECMO 起始及早期施行左心减压,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和 ECMO 及机械通气的脱机率。在 Na 等[43]的研究中,有 335 例心源性休克的成年患者经历了 V-A ECMO 支持治疗,其中有 50 例同时经历了左心减压;而在这 50 例中,有 18 例在 ECMO 转机开始时即行经皮左心减压(预防组),剩余 32 例则在出现左室功能损害的并发症时实施了治疗性的左心减压(治疗组); 相比于治疗组的 30 d 死亡率(34.4%),预防组的 30 d 死亡率为 5.6%(P=0.036),同时预防组的心脏移植或 LVAD 置入率明显高于治疗组(66.7% vs. 37.5%,P=0.048)。根据以上研究结果,越早启动左心减压,带来的益处可能更大,因此我们推断,预防性左心减压是可行且必要的,但目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加以证实。
3 小结
外周 V-A ECMO 的应用虽然可以使得许多危重症患者得以成功救治,但因为其固有的血流动力学缺陷,会形成所谓的“对冲平面”,使得 LVEDP 升高,存在继发心肺等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可能。机械性左心减压可以通过打断 LVEDP 进行性升高的血流动力学变化,起到预防和治疗上述并发症的效果,但也有研究证实左心减压操作在增加风险的同时对改善器官功能等终点指标并无益处。对于成人,在 LVEDP 升高时,适度下调 ECMO 流量、正性肌力药及扩血管药物等血管活性药物的合理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LVEDP,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接受的,只有出现严重的左心扩张时,才考虑行左心减压,即影像学上出现肺水肿、肺动脉舒张压>25 mm Hg 及室性心律不齐或左室内血液明显瘀滞时,需要行左心减压。对于儿童,由于其对左室扩张的耐受性更差,更易因此而出现心脏结构性损伤。因此,虽然有研究表明左心减压未带来明显的效果,但更多的研究倾向于积极早期减压。同时,相关证据表明,越早启动左心减压,带来的益处可能越大,因此我们推断,预防性左心减压是可行且必要的,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加以证实。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闫阳波参与文章的撰写和修改;干昌平对文章的相关内容进行指导和修正。
1 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
1.1 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的置管方式及适应证
目前,基于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的临床适应证,其置管方式可分为两大类,即静脉-静脉(V-V ECMO)型和静脉-动脉(V-A ECMO)型。V-V ECMO 的基本置管方式为经股静脉和颈静脉两个位置分别置管,在该种置管方式下,血液自股静脉引出体外,氧合后经颈静脉回输体内;近年来也有经“Y”形双极管安置导管的颈静脉单位置的置管方式。而 V-A ECMO 的最常用置管方式外周型,即置管位置为股静脉和股动脉两个位置,血液自股静脉引出,氧合后经股动脉回输入体内;但在这种置管方式下,会出现所谓的“对冲平面”,影响脑及冠状动脉的血供,因此,也有在外周型置管方式的基础上,在股动脉导管处接一“Y”形双极导管,自股动脉导管处另连导管至颈内静脉,以使氧合血可直接回到心脏并得以滋养冠状动脉及脑,该种置管方式称为 V-A-V ECMO(venoarterial-venous ECMO)[1]。因为经外周股动、静脉插管安置 V-A ECMO 操作简便,实施迅速,出血风险小,在 ICU 床旁便可完成,是目前临床上最常采用的体外生命支持模式。
总的来说,V-A ECMO 主要用于为各种病因所致心功能障碍提供短期(几天至几周)的循环支持和/或呼吸支持。ECMO 本身并不能治疗各种原发疾病,但可以支持心肺功能及改善全身脏器灌注,而且可以帮助心脏得到休息,为下一步决策争取时间,为器官功能恢复赢得机会,为心跳骤停患者评估神经系统预后,为需要心脏移植或者长时间机械循环辅助重度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提供过渡性治疗。其主要适应证有:(1)各种病因所致的心源性休克,也包括心脏术后或原发性移植物衰竭所致的心源性休克;(2)心脏骤停时与心肺复苏的联用(extracorporeal cardiopulmonary rescuscitation,ECPR);(3)难治性的室性心律失常;(4)暴发性心肌炎;(5)肺栓塞;(6)心脏移植或左室辅助装置时的过渡性治疗等[1-2]。目前 V-A EMCO 最主要的适应证仍是各种原因所致的心源性休克。急性心力衰竭是指短时间内由心脏泵功能减弱所引发的循环功能障碍,广义上也包含由此引发的多器官功能不全的临床状态。心源性休克是急性心力衰竭最为危重的表现形式,当并发急性心肌梗死时,死亡率可高达 50%~60%[3]。临床上心源性休克的定义为:收缩压≤90 mm Hg,心脏指数(CI)<2.0 L/(min·m2),左室舒张末期压力(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pressure,LVEDP)>16 mm Hg,出现组织低灌注的临床表现,伴随或不伴随乳酸升高。心源性休克期间,不仅心脏功能会继续恶化,同时由于心输出量急剧下降,全身组织器官低灌注,还有约 32% 的患者继发心脏以外的多器官功能障碍,严重影响预后[4-5]。体外生命支持这一概念及相关技术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已经在多项研究中被证实能够改善急性心力衰竭状态下难治性心跳骤停患者的死亡率和神经系统预后。心外科术后并发心源性休克的患者,使用体外生命支持可使其生存率增加约 1.5 倍[6]。体外生命支持的种类很多,包括完整的心肺转流(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ECMO 以及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等。其中 V-A ECMO 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体外生命支持类型,也是美国心脏协会(AHA)推荐用于治疗急性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的首选[7]。也有文献[8-9]报道,V-A ECMO 可应用于感染性休克治疗过程的生命支持,但相比于心源性休克,V-A ECMO 在感染性休克的支持效果远比不上心源性休克。
1.2 外周 V-A ECMO 中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及其对器官功能的影响
在最常用的外周股动、静脉置管的方式中,血液自股静脉引出体外,氧合后的血液经股动脉-髂动脉-腹主动脉-胸主动脉的血流方向进入体内,这与心脏射血方向(左室-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腹主动脉)截然相反,从而抵消一部分心脏射血的力量,形成所谓的“对冲平面”[10-11],随着左心残余功能及 ECMO 流量的不同,“对冲平面”可以出现在主动脉的任一位置。这带来的主要表现为:由于心脏射血的力量被部分抵消,左室后负荷增加,LVEDP 会升高[12],有研究[13]表明,在心源性休克状态下,ECMO 的流量分别为 1.5 L/min、3.0 L/min、4.5 L/min 时描记出的压力-容积曲线表明,LVEDP 随着 ECMO 的流量增大会逐渐升高,且 LVEDP 的变化比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LVEDV)的变化更加明显。LVEDP 的升高将进一步引发肺水肿、左室扩张、室性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心内血栓形成、多器官功能障碍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14-16]。有研究[17]发现,当狗的左房压高于 24 mm Hg 维持 30 min,可使肺水肿呈指数性增加,维持 3 h 则没有动物能够存活。可见,持续升高的左房压还将引起级联反应式的多器官功能障碍,不可逆肺水肿甚至呼吸窘迫综合征等心外器官损害,同样严重危害预后。
2 左心减压
2.1 左心减压的必要性
在外周股动、静脉置管的方式下,LVEDP 的升高会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因此,在 V-A ECMO 中,如何在充分维护脏器灌注的同时,降低左室后负荷,保证心肌充分休息和促进其恢复,避免严重心脏及心外脏器功能障碍的发生,成为 ECMO 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有研究[18]表明,适度下调 ECMO 流量、增加强心药物剂量促进心脏射血、减少缩血管药物使用等方式虽然可以不同程度地降低左室后负荷,然而这些治疗手段不但减低左室后负荷的效能极其有限,而且可能以牺牲 ECMO 效能、降低组织灌注和氧供以及增加心肌氧耗作为代价,对极度衰竭的左心来说,可能对其恢复是不利的[19]。因此近年来,更加积极的机械性左心减压手段逐渐应用于临床,包括: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房间隔造口、房间隔支架、肺动脉、左心房及左心室插管直接减压,经皮跨主动脉瓣左室减压和左心辅助装置等,不同程度地改善了患者的预后。有研究[20-21]证实,联合 ECMO 和 Impella 5.0 能够通过更充分的左心减压加快 ECMO 的成功撤离;心肌活检显示充分左心减压能够帮助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心肌恢复;早期左心减压,更能够为后续的介入诊断治疗提供更为稳定的患者状态、减少强心药物的使用、改善心肌灌注、减少心肌坏死。而其它机械性减压手段如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房间隔造口、经皮跨主动脉瓣左室减压和左心辅助装置等手段的应用,也使得 30 d 死亡率降低、血管活性药物剂量降低、ECMO 及呼吸机脱机率升高、ICU 及住院时间缩短以及心脏移植或人工心脏移植率增高等[12, 22-26]。
尽管越来越多的观察性研究肯定了在急性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状态下行 V-A ECMO 支持的患者中左心减压对某些临床指标的改善作用,但多数研究也证实其对改善器官功能以及死亡率等终点指标并无益处。Russo 等[27]的研究表明,V-A ECMO 联用左心减压时全因死亡率比不联用左心减压的患者更低(54% vs. 65%),虽然减压组溶血发生率更高,但出血、肢体缺血、肾脏替代治疗、多器官衰竭以及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在减压组和不减压组的发生率相近。同时,额外的减压,特别是外科性操作,不仅大大增加危重患者出血和感染的风险,增加 ECMO 管路的复杂程度,还大大增加治疗费用[28-31]。 因此,在考虑是否行左心减压时,筛选合适的患者可能会减轻并发症,对于心功能更具恢复能力的患者,需要更加积极的减压。Camboni 等[32]认为,在评估心功能恢复的可能性时,需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基础心脏病,急性且可治疗的急性心脏病(如心肌炎、再通的急性心肌梗死)与终末期的慢性心力衰竭相比,心功能更容易恢复;(2)支持的有效性和终末器官对氧气反应性,持续低下的静脉血氧饱和度、长期持续升高的乳酸水平和持续性酸中毒的患者具有较小的恢复潜力,而动脉血气立即恢复正常的患者则具有较大的恢复潜力;(3)超声心动图有助于识别心功能的恢复潜力,在使用 ECMO 最初的 24 h 内心室功能改善的患者比心室高度扩张、无射血、主动脉瓣关闭和心室淤滞的患者具有更大的恢复潜力。
2.2 左心减压的手段
目前,机械性左心减压的手段也已趋向于多元化。按创伤大小,则分为外科手段和经皮微创入路。外科手段通常为经胸骨正中切口、胸骨旁小切口、剑突下切口及经膈肌等入路,在右上肺静脉、肺动脉、左心耳及左心尖等部位置入引流管行左心减压;而经皮途径则经股动、静脉穿刺入路后,置入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mpella 等装置,或行房间隔造口术及经皮超声引导心房分流器植入术等手段行左心减压[23, 33-35]。但最初实施 ECMO 时绝大多数是因在床旁完成而没有开胸,或者心脏术后基于需要左心减压的考虑而延迟关胸,其难度和代价都很高,所以在外周 V-A ECMO 的情况下,可能会更倾向于介入的方法进行左心减压。
2.3 左心减压的时机
目前,减压时机和指征差别巨大,对于左心减压的时机,成人和儿童也不尽相同。
对于成人而言,由于外周 V-A ECMO 固有的血流动力学的缺陷,在其使用过程中,会引起 LVEDP 升高,除了因压力逆传引起肺水肿、急性肺损伤等并发症,也可导致左室扩张[36]。但一般认为成人对升高的 LVEDP 的耐受性较好,因此,对于 V-A ECMO 所致的左室扩张,通过适度下调 ECMO 流量、正性肌力药及扩血管药物等血管活性药物的合理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LVEDP,这时,轻度升高的 LVEDP 对于成人而言是可以接受的[18],考虑到前述的左心减压的操作会带来出血、感染等并发症,成人左心减压往往采取较保守的策略,只有在极严重的左室扩张时,才会考虑行左心减压。 Truby 等[37]将左室扩张按程度分为 3 类,分别为:(1)亚临床左室扩张(subclinical LVD,LVD+): V-A ECMO 支持后的前 2 h 内,胸部 X 线片显示肺水肿和肺动脉舒张压>25 mm Hg;(2)左室扩张(LVD++):由于肺水肿、室性心律不齐或左室内血液明显瘀滞,需要在 V-A ECMO 启动后立即进行中心减压;(3)无左室扩张(LVD–):不满足上述 LVD+的诊断标准,也不需要立即减压者。而 LVD++和 LVD+需要考虑减压,LVD–者则暂时不需要行左心减压。但 Cheng 等[38]发现在 V-A ECMO 治疗过程中,由于肺血管灌注不足,肺静脉损伤的严重程度可能会被低估,从而导致胸部 X 线片上肺水肿的表现不明显,在肺血管血流恢复后,肺水肿的影像学表现会显现出来,这提示我们,按照 Truby 等的减压标准,可能会因未能及时从胸部 X 线片上识别肺水肿而延误一部分患者的治疗。
相较于成人而言,儿童对左室扩张的耐受性更差,更易因此而出现心脏结构性损伤。因此,儿童左心减压更为积极。有些医学中心常规在 V-A ECMO 支持治疗起始时[18],最晚不超过 12 h 内联用左心减压:在 Kotani 等[39]的研究中,178 例患者使用 V-A ECMO 支持治疗,有 23 例患者经历了左房减压:其中 16 例(70%)患者在 ECMO 启动时经历了左房减压,并且在 ECMO 启动后 12 h 内所有 23 例患者经历了左房减压,结果为 ECMO 支持时间为(5.9±4.5)d,16 例(70%)患者成功脱机,ICU 生存率和医院生存率分别达到 57%和52%。Zampi 等[40]参与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通过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确定 ECMO 转机后 18 h 为早期减压与晚期减压的临界点,早期减压(V-A ECMO 支持治疗后 18 h 内行左房减压)与晚期减压(V-A ECMO 支持治疗 18 h 后行减压治疗)相比,早期减压组机械通气支持时间短于晚期减压[早期减压 10(7,15)d vs. 晚期减压 17(10,29)d,P=0.01]。Sandrio 等[41]观察到在 8 例心脏术后或心脏病所致的低心排血量的儿童患者,在机械生命支持的同时予以左室减压后,脱机率高,平均支持时间 6 d,期间未观察到心内血栓或栓塞性卒中,也未出现因颅内出血而导致体外生命支持期间和之后出现神经功能障碍。这些研究都证实了积极的左心减压可以改善患儿的预后。但是也有相反的研究结果表明,减压对于儿童未带来明显的益处:Alghanem 等[42]发现,减压虽然成功降低了平均左房压力,但减压组和对照组院内死亡率相近(29% vs. 38%,P=0.513),且减压组住院时间更长。
目前在临床上,左心减压多为在外周 V-A ECMO 并发症的治疗性手段。我们知道,在外周 V-A ECMO 治疗过程中,LVEDP 升高会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预后,那么从 ECMO 治疗起始时就积极地应用左心减压,打断上述压力逆传的过程,能否改善患者的预后呢? Kotani 等[39]及 Zampi 等[40]的研究均证实,ECMO 起始及早期施行左心减压,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和 ECMO 及机械通气的脱机率。在 Na 等[43]的研究中,有 335 例心源性休克的成年患者经历了 V-A ECMO 支持治疗,其中有 50 例同时经历了左心减压;而在这 50 例中,有 18 例在 ECMO 转机开始时即行经皮左心减压(预防组),剩余 32 例则在出现左室功能损害的并发症时实施了治疗性的左心减压(治疗组); 相比于治疗组的 30 d 死亡率(34.4%),预防组的 30 d 死亡率为 5.6%(P=0.036),同时预防组的心脏移植或 LVAD 置入率明显高于治疗组(66.7% vs. 37.5%,P=0.048)。根据以上研究结果,越早启动左心减压,带来的益处可能更大,因此我们推断,预防性左心减压是可行且必要的,但目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加以证实。
3 小结
外周 V-A ECMO 的应用虽然可以使得许多危重症患者得以成功救治,但因为其固有的血流动力学缺陷,会形成所谓的“对冲平面”,使得 LVEDP 升高,存在继发心肺等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可能。机械性左心减压可以通过打断 LVEDP 进行性升高的血流动力学变化,起到预防和治疗上述并发症的效果,但也有研究证实左心减压操作在增加风险的同时对改善器官功能等终点指标并无益处。对于成人,在 LVEDP 升高时,适度下调 ECMO 流量、正性肌力药及扩血管药物等血管活性药物的合理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LVEDP,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接受的,只有出现严重的左心扩张时,才考虑行左心减压,即影像学上出现肺水肿、肺动脉舒张压>25 mm Hg 及室性心律不齐或左室内血液明显瘀滞时,需要行左心减压。对于儿童,由于其对左室扩张的耐受性更差,更易因此而出现心脏结构性损伤。因此,虽然有研究表明左心减压未带来明显的效果,但更多的研究倾向于积极早期减压。同时,相关证据表明,越早启动左心减压,带来的益处可能越大,因此我们推断,预防性左心减压是可行且必要的,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加以证实。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闫阳波参与文章的撰写和修改;干昌平对文章的相关内容进行指导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