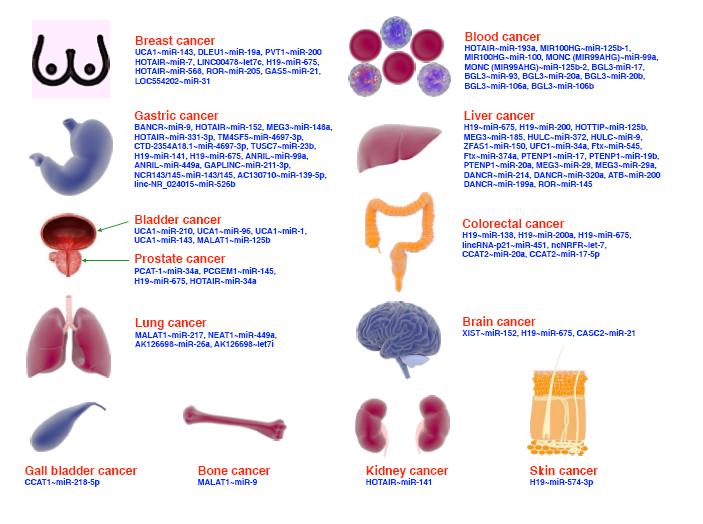肺癌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之一,是一种极具挑战的复杂疾病。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这些挑战。本综述旨在探讨COVID-19疫情对肺癌筛查、诊断和治疗的影响,希望能够为肺癌患者的全程管理提供一些经验和帮助。
引用本文: 孟于琪, 李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肺癌患者诊疗的影响.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3, 30(4): 635-640. doi: 10.7507/1007-4848.202301006 复制
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为全球大流行。此后,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呈指数增长,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疫情。目前COVID-19已持续3年,影响到全球医疗系统的方方面面。截至2022年11月25日,全球已有6.36亿多例COVID-19确诊病例,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近660万例死亡病例。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引起的COVID-19大流行成为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大流行之一。虽然全球各个国家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SARS-CoV-2疫苗,但是病毒不断变异导致疫苗的保护能力下降。
癌症患者是一个异质性人群,因其常合并凝血功能紊乱(高凝状态)、免疫功能受损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姑息性治疗等,在感染COVID-19后往往更加容易出现临床并发症和进展为危重症[1-3]。在我国,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肿瘤[4],同时肺是SARS-CoV-2主要攻击的靶器官[5]。因此,COVID-19对肺癌患者的影响值得我们重点关注。本文根据现有证据重点介绍COVID-19对肺癌的发病率、诊断和治疗的影响。
1 肺癌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因发病率统计需要的样本量较大,所以对于肺癌患者是否容易感染COVID-19的数据较少。有研究[6-8]认为,肺癌患者容易感染COVID-19,风险比(hazard ratio,HR)为1.51~7.66(P均<0.05)。其中来自美国的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8]发现,已接种疫苗的肺癌患者比非癌症患者发生突破性COVID-19感染的风险更高[HR=1.73,95%CI(1.50,1.99),P<0.05]。还有研究[1]仅观察到肺癌患者容易感染COVID-19,但因为病例数太少没有获得HR值。因此,肺癌患者感染COVID-19的风险是否更高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对于肺癌患者感染COVID-19后更易患重症肺炎(需进重症监护室/机械辅助通气或威胁生命安全)的研究争议较大。一些研究[9-12]认为,与非肿瘤人群相比肺癌患者更容易得重症肺炎,HR可达4.28[95%CI(1.44,12.72)][9]。然而另外一些研究[13-14]认为肺癌患者和非肿瘤人群患重症肺炎的风险没有明显差异。Beltramo等[15]的研究甚至认为,肺癌患者患重症肺炎的风险比非肿瘤人群小[HR=0.77,95%CI(0.63,0.94)]。这些研究纳入的病例数均较少而且混杂因素较多(如接受抗肿瘤治疗方案的差异、年龄、吸烟状态和其他合并症等),目前无法明确肺癌患者感染COVID-19后是否更容易患重症肺炎。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肺癌诊断的影响
COVID-19引起的肺炎初期CT影像学表现主要为磨玻璃影(ground-glass opacity,GGO)和实变影或者两者均有[16]。而COVID-19痊愈1年后仍有56.7%的患者肺部CT有异常,包括GGO、支气管扩张、结节、纤维条索、纤维化等[17]。这些影像学表现和早期肺癌或肺癌进展的CT表现相同,因此COVID-19对肺癌诊断的影响值得更进一步研究。
荷兰国家癌症登记系统数据[18]显示,2020年3月—5月期间新发癌症患者减少约25%。而在英国,疑似癌症病例的转诊在疫情期间减少了约80%[19-20]。一项来自西班牙的回顾性队列研究[21]指出,与COVID-19之前(2019年1月—6月)相比,COVID-19期间(2020年1月—6月)肺癌新确诊病例数下降38%。韩国的一项研究[22]比较了疫情期间翰林大学3家附属医院疫情期间与此前3年同期新确诊肺癌病例,结果显示,Ⅲ~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比例显著增加(2020年vs. 2017年vs. 2018年vs. 2019年:74.7% vs. 57.9% vs. 66.7% vs. 62.7%,P=0.011),而早期癌症患者比例在疫情期间有所下降。这提示疫情期间,肺癌新确诊病例数下降并且诊断存在延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疫情期间很多患者担心感染COVID-19而不愿就医或推迟原有健康体检计划导致肺癌的诊断延迟。这种情况在高龄、存在多种合并症和吸烟史的肺癌高发人群以及已诊断为肺癌的患者中更为常见[23]。英国肺癌联盟的一项报告[24]提示,英国政府在COVID-19期间非急诊避免就医的建议强烈影响了患者就医的动机和意愿。同样地,2003年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台湾的一项研究[25]表明,在参加肺癌临床试验的患者中约64%的患者因害怕感染而不愿就医,约4%的患者决定暂停所有治疗。
其次,医疗资源紧张也是重要原因。随着需要住院治疗的COVID-19患者数量增加,医疗资源的挤兑和医护人力资源重新分配是许多医疗机构的普遍现象[26]。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的临床研究面临中断的风险。例如,在韩国翰林大学的3家附属教学医院中,普通癌症诊断领域的工作人员被分配到COVID-19筛查病房,以解决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22]。这些医疗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给接诊肺癌的临床医护人员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工作压力。
总体来说,COVID-19对肺癌诊断的影响尚无大数据评估。英国国内估计COVID-19导致的诊断延迟可能使得超过1 000例肺癌患者在明确诊断后的5年内死亡,这可能逆转近年来在肺癌生存率方面取得的进展[19]。这些结果需长时间和大样本研究进一步观察。
3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肺癌治疗的影响
目前肺癌的治疗方案主要包括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本节将介绍COVID-19对上述肺癌治疗方案的影响。
3.1 COVID-19对肺癌手术的影响
对于疫情期间可手术肺癌患者是否首先推荐手术治疗仍存在争议。国际肺癌学会建议COVID-19大流行期间提供安全的肺部手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标准治疗[27]。相反,瑞士南部肿瘤研究所肺癌中心建议对癌症进展风险高(T4期任意N、N2期任意T转移和寡转移)和COVID-19感染风险高(年龄>70岁、有免疫抑制或>2项合并症)的患者采用完全非手术治疗[28]。
根据患者的肿瘤分期通过多学科讨论来共同决策是对患者负责的决策方式。根据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数据,术前诊断为Ⅰ期肺癌的患者,诊断和手术的间隔时间>8周可能影响患者生存[29]。国际癌症研究协会根据此项研究结果也推荐诊断和手术的间隔时间不应超过6~8周[30]。近期一项研究[31]认为对于Ⅰ期肺癌患者,诊断和手术的间隔时间<14 d是最优选择,>30 d提示预后欠佳。Ⅰ期肺癌人群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对于肿瘤直径<2 cm、以GGO成分为主(实性成分<50%)或术前病理证实为惰性肿瘤(如类癌)的短期内疾病进展风险较小的患者是否可延迟手术,目前尚无数据支持。Thoracic Surgery Outcomes Research Network(ThORN)[32]和美国外科医师协会[33]均推荐对肺癌患者分类诊治。对于直径<2 cm的实性结节或GGO为主(实性成分<50%)的结节可以暂缓手术,最长不超过3个月。对于直径>2 cm的实性和以实性成分为主(实性成分>50%)的结节患者或怀疑淋巴结阳性患者应在“数周”内尽快手术,但是具体时间没有定义。作者建议对于短期内进展风险较小的Ⅰ期肺癌患者尽可能在诊断后8周内完成手术治疗,其余患者应尽可能在诊断后4周内完成手术。对于术前诊断Ⅱ~ⅢA期可根治切除的患者,诊断和手术之间的间隔时间尚无数据支持,美国肺癌领域专家共识[30]建议对于Ⅱ~ⅢA期可切除的患者或完成术前新辅助治疗的患者在4周内完成手术治疗;对于肺癌合并COVID-19的患者如果条件允许建议推迟2~3周,待COVID-19治愈(鼻拭子核酸检测阴性,如果合并肺炎患者应复查胸部CT明确病灶已明显吸收或完全消失)后进行手术。现有证据提示亚肺叶切除在COVID-19大流行阶段可能优于肺叶切除。在术后感染COVID-19的11例患者中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34]提示,病死率与切除≥5个肺段显著相关。一些学者[35]认为COVID-19大流行期间,亚肺叶切除术后快速康复的益处可能超过癌症复发的风险,尤其是考虑到疫情后再次行解剖性切除的可能性。特别是术前功能储备有限的患者可能从亚肺叶切除中获益[36]。
关于COVID-19康复后行肺癌根治术的患者术后病理情况的报道相对较少,目前仅检索到4例个案报道[37-39]。这4例患者的COVID-19治愈标准都为鼻拭子阴性并且肺部影像学较前明显好转或病灶消失,手术时间在肺炎治愈后4~7周。4例患者非肿瘤区域肺组织中发现了炎症细胞浸润、肺泡中幼稚成纤维细胞浸润和肉芽组织生长等肺炎后纤维化的早期表现。2例患者肿瘤周围组织弥漫性肺泡损伤[37],1例患者在之前肺部感染区域通过RT-PCR仍检出SARS-CoV-2[39]。
在COVID-19疫情期间肺癌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尤为重要。常规建议术前1 d行鼻拭子检测,避免无症状感染者接受手术治疗[30]。肺癌手术后感染COVID-19的病死率非常高,细致的临床监测和分诊至关重要[35]。由于呼吸急促、咳嗽、发热和疲劳等,COVID-19症状与肺部手术后的常见临床表现重叠,COVID-19的诊断可能会进一步延迟[34]。这种情况要求外科医师、呼吸科医师和全科医师密切关注潜在SARS-CoV-2感染的临床体征,如果有疑问,则及时采集鼻咽拭子检测[34]。
3.2 COVID-19对肺癌化疗和靶向治疗的影响
化疗会加重肺癌患者合并COVID-19的疾病程度。一项研究[10]表明,COVID-19合并肺癌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增加,预后较差。另一项研究[40]表明接受细胞毒性化疗的患者发生COVID-19重症的风险较高。COVID-19大流行为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带来了额外挑战。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均建议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需积极预防化疗带来的骨髓抑制,并且为较低风险患者开具生长因子类处方是合理的[41-43]。
然而骨髓抑制常用药物“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可能导致COVID-19患者更严重的结局,原因可能是肺部炎症和巨噬细胞活化增加[41, 44],而且COVID-19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以炎症标志物(包括G-CSF)水平升高为特征的“细胞因子风暴”[45]。最近几年新上市或正在临床研究中的药物可提供更多的选择,如Trilaciclib、Plinabulin、Avatrombopag、Romiplostin等。
肺癌靶向治疗主要药物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其引起的肺炎为间质性肺炎。接受奥西替尼治疗的患者中间质性肺炎的发生率约为4%[46],这给COVID-19的诊断带来困扰。因此很多专家建议COVID-19感染期间停药,待患者治愈(鼻拭子阴性,对于合并肺部感染患者行胸部CT检查明确肺部感染病灶已明显好转或完全消失)后继续服用药物[47]。但个案报道[48]提示,肺癌患者在COVID-19感染治疗期间继续服用阿来替尼是安全的。关于COVID-19感染期间停药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目前尚无数据,需要在后续的临床工作中继续观察。
需要注意的是治疗COVID-19的特效药物(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的抗病毒活性成分利托那韦是强细胞色素P450 3A4(CYP 3A4)抑制剂。许多针对癌症的口服靶向药物是已知的CYP 3A4底物,与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同时使用可能会导致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目前尚未在临床观察到两者的相互作用,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监测。
3.3 COVID-19对肺癌免疫治疗的影响
已经在多种癌症中证明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程序性死亡受体-1配体(programmed cell death-1 ligand,PD-L1)抑制剂可以提高患者生存率,但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癌症患者的影响仍有待确定[49]。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诱发的免疫性肺炎发生率>2%[49]。免疫治疗诱发的肺炎CT影像学表现与COVID-19诱发的肺炎相似,这可能给临床医师鉴别这两种临床疾病带来重大挑战[47]。理论上阻断PD-1/PD-L1可能会导致两种结局:一方面可能会加剧COVID-19引起的过度活跃免疫反应从而恶化结局;另一方面可能增强对病毒感染的免疫控制并改善结局[50-51]。
在一项纳入69例肺癌门诊患者的单中心观察性研究[52]中,未发现既往免疫治疗与COVID-19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关联。但是鼻拭子核酸检测阳性患者接受免疫治疗会明显增加严重不良反应[53]。考虑到免疫治疗带来的抗肿瘤获益,欧洲肿瘤医学会专家建议在无COVID-19感染的情况下不应推迟或放弃免疫治疗。对于COVID-19感染患者应在感染治愈(鼻拭子阴性,如果肺部有炎症还应复查胸部CT明确感染病灶已明显吸收或完全消失)后重新开始治疗[54]。
有学者[55]提出了加大单次剂量并延长治疗间隔时间的治疗模式。与标准治疗模式相比,加大单次剂量并延长间隔时间并没有增加患者的不良反应,无疾病生存和总生存也没有劣势。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种治疗模式减少了患者住院次数,缩短了住院时间,是一种可选的治疗模式,但仍需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
3.4 COVID-19对肺癌放疗的影响
放疗的延迟或缺失可能会对肺癌患者的结局产生负面影响。考虑到患者的高龄、合并症以及治疗的不良反应,接受放疗的肺癌患者属于COVID-19相关死亡风险最高的人群。
COVID-19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和放疗引起的放射性肺炎影像学表现和临床症状都非常相似[56]。临床症状均有低氧血症、刺激性干咳和发热,但是放射性肺炎的症状通常在放射线暴露后6个月左右出现[57]。两者的影像学表现均可出现GGO,但是放射性肺炎通常是单侧而且和放射野高度相关[58]。放射性肺炎患者感染COVID-19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表现尚无文献报道,在临床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观察。
一项纳入1 553例接受放疗的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59]发现,34%的患者改变了治疗方案,而且正在接受放疗或者已经完成放疗的患者中只有1.4%的患者感染了COVID-19,这一比例低于其他肺癌患者(2.1%)。这可能和患者自身防护加强、大分割放疗方案的实施有关。目前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肺癌患者接受放疗的获益情况尚无高级别证据证实。欧洲放疗肿瘤学会和美国放射肿瘤学会肺癌放疗国际专家小组认为,COVID-19大流行期间,在放疗资源仍然可用的情况下,应采用指南建议的放疗方案,并推迟COVID-19阳性患者的放疗,以保护癌症患者和工作人员[60]。另有学者[61]认为,减少放疗分割次数的大分割方案是可选择的方案。
在疫情期间早期肺癌是否可采用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代替手术存在争议。欧洲肿瘤医学会推荐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于Ⅰ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手术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可以用SBRT代替手术[54]。然而另一项研究[31]发现SBRT的远期预后明显较手术差,即使因疫情影响将手术推迟90 d,手术效果也优于SBRT。因此在临床工作中选择SBRT代替手术时应慎重。
4 总结与展望
肺癌患者易感染COVID-19,且重症感染者比例较高。COVID-19给肺癌患者筛查、诊断和治疗均带来挑战。对于合并COVID-19的肺癌患者应适当推迟抗肿瘤治疗,在COVID-19治愈后应尽快开始原有治疗方案。未感染或既往感染COVID-19的肺癌患者不应轻易中断或改变治疗方案。通过多学科讨论机制根据患者的年龄、体质和肿瘤分期等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非常重要。而且SARS-CoV-2病毒在不断的变化中,我们需要不断根据病毒变化和国家防疫政策的变化来调整肺癌患者治疗方案和治疗模式。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孟于琪负责文章撰写及修改;李斌负责审校。
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为全球大流行。此后,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呈指数增长,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疫情。目前COVID-19已持续3年,影响到全球医疗系统的方方面面。截至2022年11月25日,全球已有6.36亿多例COVID-19确诊病例,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近660万例死亡病例。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引起的COVID-19大流行成为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大流行之一。虽然全球各个国家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SARS-CoV-2疫苗,但是病毒不断变异导致疫苗的保护能力下降。
癌症患者是一个异质性人群,因其常合并凝血功能紊乱(高凝状态)、免疫功能受损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姑息性治疗等,在感染COVID-19后往往更加容易出现临床并发症和进展为危重症[1-3]。在我国,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肿瘤[4],同时肺是SARS-CoV-2主要攻击的靶器官[5]。因此,COVID-19对肺癌患者的影响值得我们重点关注。本文根据现有证据重点介绍COVID-19对肺癌的发病率、诊断和治疗的影响。
1 肺癌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因发病率统计需要的样本量较大,所以对于肺癌患者是否容易感染COVID-19的数据较少。有研究[6-8]认为,肺癌患者容易感染COVID-19,风险比(hazard ratio,HR)为1.51~7.66(P均<0.05)。其中来自美国的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8]发现,已接种疫苗的肺癌患者比非癌症患者发生突破性COVID-19感染的风险更高[HR=1.73,95%CI(1.50,1.99),P<0.05]。还有研究[1]仅观察到肺癌患者容易感染COVID-19,但因为病例数太少没有获得HR值。因此,肺癌患者感染COVID-19的风险是否更高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对于肺癌患者感染COVID-19后更易患重症肺炎(需进重症监护室/机械辅助通气或威胁生命安全)的研究争议较大。一些研究[9-12]认为,与非肿瘤人群相比肺癌患者更容易得重症肺炎,HR可达4.28[95%CI(1.44,12.72)][9]。然而另外一些研究[13-14]认为肺癌患者和非肿瘤人群患重症肺炎的风险没有明显差异。Beltramo等[15]的研究甚至认为,肺癌患者患重症肺炎的风险比非肿瘤人群小[HR=0.77,95%CI(0.63,0.94)]。这些研究纳入的病例数均较少而且混杂因素较多(如接受抗肿瘤治疗方案的差异、年龄、吸烟状态和其他合并症等),目前无法明确肺癌患者感染COVID-19后是否更容易患重症肺炎。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肺癌诊断的影响
COVID-19引起的肺炎初期CT影像学表现主要为磨玻璃影(ground-glass opacity,GGO)和实变影或者两者均有[16]。而COVID-19痊愈1年后仍有56.7%的患者肺部CT有异常,包括GGO、支气管扩张、结节、纤维条索、纤维化等[17]。这些影像学表现和早期肺癌或肺癌进展的CT表现相同,因此COVID-19对肺癌诊断的影响值得更进一步研究。
荷兰国家癌症登记系统数据[18]显示,2020年3月—5月期间新发癌症患者减少约25%。而在英国,疑似癌症病例的转诊在疫情期间减少了约80%[19-20]。一项来自西班牙的回顾性队列研究[21]指出,与COVID-19之前(2019年1月—6月)相比,COVID-19期间(2020年1月—6月)肺癌新确诊病例数下降38%。韩国的一项研究[22]比较了疫情期间翰林大学3家附属医院疫情期间与此前3年同期新确诊肺癌病例,结果显示,Ⅲ~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比例显著增加(2020年vs. 2017年vs. 2018年vs. 2019年:74.7% vs. 57.9% vs. 66.7% vs. 62.7%,P=0.011),而早期癌症患者比例在疫情期间有所下降。这提示疫情期间,肺癌新确诊病例数下降并且诊断存在延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疫情期间很多患者担心感染COVID-19而不愿就医或推迟原有健康体检计划导致肺癌的诊断延迟。这种情况在高龄、存在多种合并症和吸烟史的肺癌高发人群以及已诊断为肺癌的患者中更为常见[23]。英国肺癌联盟的一项报告[24]提示,英国政府在COVID-19期间非急诊避免就医的建议强烈影响了患者就医的动机和意愿。同样地,2003年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台湾的一项研究[25]表明,在参加肺癌临床试验的患者中约64%的患者因害怕感染而不愿就医,约4%的患者决定暂停所有治疗。
其次,医疗资源紧张也是重要原因。随着需要住院治疗的COVID-19患者数量增加,医疗资源的挤兑和医护人力资源重新分配是许多医疗机构的普遍现象[26]。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的临床研究面临中断的风险。例如,在韩国翰林大学的3家附属教学医院中,普通癌症诊断领域的工作人员被分配到COVID-19筛查病房,以解决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22]。这些医疗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给接诊肺癌的临床医护人员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工作压力。
总体来说,COVID-19对肺癌诊断的影响尚无大数据评估。英国国内估计COVID-19导致的诊断延迟可能使得超过1 000例肺癌患者在明确诊断后的5年内死亡,这可能逆转近年来在肺癌生存率方面取得的进展[19]。这些结果需长时间和大样本研究进一步观察。
3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肺癌治疗的影响
目前肺癌的治疗方案主要包括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本节将介绍COVID-19对上述肺癌治疗方案的影响。
3.1 COVID-19对肺癌手术的影响
对于疫情期间可手术肺癌患者是否首先推荐手术治疗仍存在争议。国际肺癌学会建议COVID-19大流行期间提供安全的肺部手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标准治疗[27]。相反,瑞士南部肿瘤研究所肺癌中心建议对癌症进展风险高(T4期任意N、N2期任意T转移和寡转移)和COVID-19感染风险高(年龄>70岁、有免疫抑制或>2项合并症)的患者采用完全非手术治疗[28]。
根据患者的肿瘤分期通过多学科讨论来共同决策是对患者负责的决策方式。根据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数据,术前诊断为Ⅰ期肺癌的患者,诊断和手术的间隔时间>8周可能影响患者生存[29]。国际癌症研究协会根据此项研究结果也推荐诊断和手术的间隔时间不应超过6~8周[30]。近期一项研究[31]认为对于Ⅰ期肺癌患者,诊断和手术的间隔时间<14 d是最优选择,>30 d提示预后欠佳。Ⅰ期肺癌人群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对于肿瘤直径<2 cm、以GGO成分为主(实性成分<50%)或术前病理证实为惰性肿瘤(如类癌)的短期内疾病进展风险较小的患者是否可延迟手术,目前尚无数据支持。Thoracic Surgery Outcomes Research Network(ThORN)[32]和美国外科医师协会[33]均推荐对肺癌患者分类诊治。对于直径<2 cm的实性结节或GGO为主(实性成分<50%)的结节可以暂缓手术,最长不超过3个月。对于直径>2 cm的实性和以实性成分为主(实性成分>50%)的结节患者或怀疑淋巴结阳性患者应在“数周”内尽快手术,但是具体时间没有定义。作者建议对于短期内进展风险较小的Ⅰ期肺癌患者尽可能在诊断后8周内完成手术治疗,其余患者应尽可能在诊断后4周内完成手术。对于术前诊断Ⅱ~ⅢA期可根治切除的患者,诊断和手术之间的间隔时间尚无数据支持,美国肺癌领域专家共识[30]建议对于Ⅱ~ⅢA期可切除的患者或完成术前新辅助治疗的患者在4周内完成手术治疗;对于肺癌合并COVID-19的患者如果条件允许建议推迟2~3周,待COVID-19治愈(鼻拭子核酸检测阴性,如果合并肺炎患者应复查胸部CT明确病灶已明显吸收或完全消失)后进行手术。现有证据提示亚肺叶切除在COVID-19大流行阶段可能优于肺叶切除。在术后感染COVID-19的11例患者中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34]提示,病死率与切除≥5个肺段显著相关。一些学者[35]认为COVID-19大流行期间,亚肺叶切除术后快速康复的益处可能超过癌症复发的风险,尤其是考虑到疫情后再次行解剖性切除的可能性。特别是术前功能储备有限的患者可能从亚肺叶切除中获益[36]。
关于COVID-19康复后行肺癌根治术的患者术后病理情况的报道相对较少,目前仅检索到4例个案报道[37-39]。这4例患者的COVID-19治愈标准都为鼻拭子阴性并且肺部影像学较前明显好转或病灶消失,手术时间在肺炎治愈后4~7周。4例患者非肿瘤区域肺组织中发现了炎症细胞浸润、肺泡中幼稚成纤维细胞浸润和肉芽组织生长等肺炎后纤维化的早期表现。2例患者肿瘤周围组织弥漫性肺泡损伤[37],1例患者在之前肺部感染区域通过RT-PCR仍检出SARS-CoV-2[39]。
在COVID-19疫情期间肺癌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尤为重要。常规建议术前1 d行鼻拭子检测,避免无症状感染者接受手术治疗[30]。肺癌手术后感染COVID-19的病死率非常高,细致的临床监测和分诊至关重要[35]。由于呼吸急促、咳嗽、发热和疲劳等,COVID-19症状与肺部手术后的常见临床表现重叠,COVID-19的诊断可能会进一步延迟[34]。这种情况要求外科医师、呼吸科医师和全科医师密切关注潜在SARS-CoV-2感染的临床体征,如果有疑问,则及时采集鼻咽拭子检测[34]。
3.2 COVID-19对肺癌化疗和靶向治疗的影响
化疗会加重肺癌患者合并COVID-19的疾病程度。一项研究[10]表明,COVID-19合并肺癌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增加,预后较差。另一项研究[40]表明接受细胞毒性化疗的患者发生COVID-19重症的风险较高。COVID-19大流行为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带来了额外挑战。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均建议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需积极预防化疗带来的骨髓抑制,并且为较低风险患者开具生长因子类处方是合理的[41-43]。
然而骨髓抑制常用药物“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可能导致COVID-19患者更严重的结局,原因可能是肺部炎症和巨噬细胞活化增加[41, 44],而且COVID-19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以炎症标志物(包括G-CSF)水平升高为特征的“细胞因子风暴”[45]。最近几年新上市或正在临床研究中的药物可提供更多的选择,如Trilaciclib、Plinabulin、Avatrombopag、Romiplostin等。
肺癌靶向治疗主要药物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其引起的肺炎为间质性肺炎。接受奥西替尼治疗的患者中间质性肺炎的发生率约为4%[46],这给COVID-19的诊断带来困扰。因此很多专家建议COVID-19感染期间停药,待患者治愈(鼻拭子阴性,对于合并肺部感染患者行胸部CT检查明确肺部感染病灶已明显好转或完全消失)后继续服用药物[47]。但个案报道[48]提示,肺癌患者在COVID-19感染治疗期间继续服用阿来替尼是安全的。关于COVID-19感染期间停药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目前尚无数据,需要在后续的临床工作中继续观察。
需要注意的是治疗COVID-19的特效药物(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的抗病毒活性成分利托那韦是强细胞色素P450 3A4(CYP 3A4)抑制剂。许多针对癌症的口服靶向药物是已知的CYP 3A4底物,与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同时使用可能会导致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目前尚未在临床观察到两者的相互作用,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监测。
3.3 COVID-19对肺癌免疫治疗的影响
已经在多种癌症中证明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程序性死亡受体-1配体(programmed cell death-1 ligand,PD-L1)抑制剂可以提高患者生存率,但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癌症患者的影响仍有待确定[49]。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诱发的免疫性肺炎发生率>2%[49]。免疫治疗诱发的肺炎CT影像学表现与COVID-19诱发的肺炎相似,这可能给临床医师鉴别这两种临床疾病带来重大挑战[47]。理论上阻断PD-1/PD-L1可能会导致两种结局:一方面可能会加剧COVID-19引起的过度活跃免疫反应从而恶化结局;另一方面可能增强对病毒感染的免疫控制并改善结局[50-51]。
在一项纳入69例肺癌门诊患者的单中心观察性研究[52]中,未发现既往免疫治疗与COVID-19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关联。但是鼻拭子核酸检测阳性患者接受免疫治疗会明显增加严重不良反应[53]。考虑到免疫治疗带来的抗肿瘤获益,欧洲肿瘤医学会专家建议在无COVID-19感染的情况下不应推迟或放弃免疫治疗。对于COVID-19感染患者应在感染治愈(鼻拭子阴性,如果肺部有炎症还应复查胸部CT明确感染病灶已明显吸收或完全消失)后重新开始治疗[54]。
有学者[55]提出了加大单次剂量并延长治疗间隔时间的治疗模式。与标准治疗模式相比,加大单次剂量并延长间隔时间并没有增加患者的不良反应,无疾病生存和总生存也没有劣势。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种治疗模式减少了患者住院次数,缩短了住院时间,是一种可选的治疗模式,但仍需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
3.4 COVID-19对肺癌放疗的影响
放疗的延迟或缺失可能会对肺癌患者的结局产生负面影响。考虑到患者的高龄、合并症以及治疗的不良反应,接受放疗的肺癌患者属于COVID-19相关死亡风险最高的人群。
COVID-19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和放疗引起的放射性肺炎影像学表现和临床症状都非常相似[56]。临床症状均有低氧血症、刺激性干咳和发热,但是放射性肺炎的症状通常在放射线暴露后6个月左右出现[57]。两者的影像学表现均可出现GGO,但是放射性肺炎通常是单侧而且和放射野高度相关[58]。放射性肺炎患者感染COVID-19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表现尚无文献报道,在临床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观察。
一项纳入1 553例接受放疗的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59]发现,34%的患者改变了治疗方案,而且正在接受放疗或者已经完成放疗的患者中只有1.4%的患者感染了COVID-19,这一比例低于其他肺癌患者(2.1%)。这可能和患者自身防护加强、大分割放疗方案的实施有关。目前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肺癌患者接受放疗的获益情况尚无高级别证据证实。欧洲放疗肿瘤学会和美国放射肿瘤学会肺癌放疗国际专家小组认为,COVID-19大流行期间,在放疗资源仍然可用的情况下,应采用指南建议的放疗方案,并推迟COVID-19阳性患者的放疗,以保护癌症患者和工作人员[60]。另有学者[61]认为,减少放疗分割次数的大分割方案是可选择的方案。
在疫情期间早期肺癌是否可采用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代替手术存在争议。欧洲肿瘤医学会推荐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于Ⅰ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手术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可以用SBRT代替手术[54]。然而另一项研究[31]发现SBRT的远期预后明显较手术差,即使因疫情影响将手术推迟90 d,手术效果也优于SBRT。因此在临床工作中选择SBRT代替手术时应慎重。
4 总结与展望
肺癌患者易感染COVID-19,且重症感染者比例较高。COVID-19给肺癌患者筛查、诊断和治疗均带来挑战。对于合并COVID-19的肺癌患者应适当推迟抗肿瘤治疗,在COVID-19治愈后应尽快开始原有治疗方案。未感染或既往感染COVID-19的肺癌患者不应轻易中断或改变治疗方案。通过多学科讨论机制根据患者的年龄、体质和肿瘤分期等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非常重要。而且SARS-CoV-2病毒在不断的变化中,我们需要不断根据病毒变化和国家防疫政策的变化来调整肺癌患者治疗方案和治疗模式。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孟于琪负责文章撰写及修改;李斌负责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