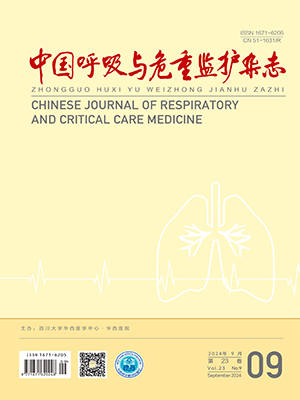引用本文: 沈凌, 陈灏, 王利民. 原发于颅内的血管周细胞瘤术后肺转移一例.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4, 13(6): 617-619. doi: 10.7507/1671-6205.2014153 复制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45岁。因“声音嘶哑、构音障碍”于2001年就诊于本院。予头颅磁共振(MRI)检查示“枕大孔区占位”,患者拒绝手术治疗。患者到外院行伽玛刀颅脑放射治疗后,症状得到明显缓解。此后每年行头颅MRI复查,显示肿块逐渐缩小。2004年患者再次出现颈部酸胀感,无肢体麻木无力,在外院诊断为“颈椎病”,进行颈椎牵引治疗,症状未得到改善。在本院经头颅MRI检查后示“枕大孔区肿块明显增大,颅外椎管内出现占位病灶,颈静脉孔扩大,局部骨质破坏,内见一实质性软组织肿块影,延椎间孔生长,第1、2颈椎水平椎动脉被肿块包绕,肿块与颈内动脉的间隙尚清晰。患者再次到外院行伽玛刀颅脑放射治疗,但此次症状缓解不明显。既往体健,个人史及家族史无特殊。血常规、生化、血肿瘤指标均正常,胸部X线片、上腹部及泌尿系统B超均正常。2005年4月在本院进行了全身麻醉下的颈椎C1~C3硬脊膜外椎管内肿瘤切除术,术中发现枕大孔与颈1间隙以及颈2~颈3间隙均有肿瘤组织突出椎管,张力增高;颈1和颈2左侧椎板被肿瘤浸润破损。术后病理示血管周细胞瘤。术后7年间患者又进行5次放射治疗和1次伽玛刀治疗,病情尚平稳。
2012年7月25日患者无诱因下突发头晕,伴恶心、呕吐2次,饮水呛咳,无肢体抽搐、耳鸣眩晕、头痛,再次就诊本院。查体:血压118/77 mm Hg(1 mm Hg=0.133 kPa),脉搏96次/min,呼吸20次/min。 神志清楚,步态正常,对答切题。左眼闭合不全,右侧眼睑、口角不自主抽动,眼球活动自如,无眼球震颤;左侧鼻唇沟变浅,口角右歪,伸舌左偏,左侧舌肌萎缩。颈抵抗,克氏征阴性和布氏征阴性。双肺呼吸音粗,两下肺可闻及细小湿啰音。心脏腹部体检正常,四肢肌力和肌张力均正常,病理征阴性。
辅助检查:血常规、生化及肿瘤指标均在正常。上腹部B超检查示肝脏多发低回声团块。甲状腺B超检查示甲状腺右侧叶多发结节。头颅MRI检查示蝶窦、斜坡、岩尖、左侧桥小脑区、颈4平面椎管内硬膜外可见多发肿块影,增强后可见外周强化,内部见不规则扭曲的血管影(图 1)。胸部CT检查示两肺多发结节和肿块影,边缘清楚、内部密度均匀,少数直径>5 cm,以两下肺为主,纵隔淋巴结无肿大(图 2和图 3)。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术获取肺组织,病理显示高密度的肿瘤细胞聚集,大小较一致,细胞间可见扩张血管,其间肿瘤细胞周围有丰富的网状纤维围绕;免疫组化示波形蛋白(+)、CD34(+)、结蛋白灶性(+),EMA(-)、S-100(-),诊断:血管周细胞瘤(图 4和图 5)。临床诊断为颅内血管周细胞瘤复发伴肺和肝脏转移。患者明确诊断后自动出院,随访1年后死亡。
 图1
颅脑MRI检查 a.横断面示颅内多发边界清晰的球形影,增强后可见个带环形强化,内有不规则密度增高的钙化影;b.矢状位
图1
颅脑MRI检查 a.横断面示颅内多发边界清晰的球形影,增强后可见个带环形强化,内有不规则密度增高的钙化影;b.矢状位
 图2
胸部CT检查 肺窗示两肺弥漫分布大小不等类圆形结节影和少量肿块,边界清楚
图2
胸部CT检查 肺窗示两肺弥漫分布大小不等类圆形结节影和少量肿块,边界清楚
 图3
胸部CT检查 纵隔窗示两肺弥漫大小不等结节,密度均匀,与肺窗相比体积略小,纵隔淋巴结无肿大
图3
胸部CT检查 纵隔窗示两肺弥漫大小不等结节,密度均匀,与肺窗相比体积略小,纵隔淋巴结无肿大
 图4
高密度的肿瘤细胞间可见扩张血管(HE ×100)
图4
高密度的肿瘤细胞间可见扩张血管(HE ×100)
 图5
肿瘤细胞和内皮细胞CD34阳性(免疫组化 ×400)
图5
肿瘤细胞和内皮细胞CD34阳性(免疫组化 ×400)
讨论 脑膜血管周细胞瘤(haemangiopericytoma,HPC)是一种少见的中枢神经肿瘤,约占所有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0.4%,其与脑膜瘤的发病率之比为1 ∶40~1 ∶60,平均发病年龄为43岁,男女发病率之比为1.4 ∶1[1]。发病部位主要位于颅内,少数位于脊髓;通常与硬脑脊膜相连。临床表现多样,与病灶的部位相关,部分患者可表现为急性颅内出血。本患者也因肿瘤复发的部位改变而出现不同的临床表现。脑膜HPC在CT和MRI上边界清楚,附于硬脑膜,边缘光滑或呈结节状,增强后可以强化,瘤周存在细胞溶解性骨质破坏,一般无钙化[2]。
脑膜HPC主要需与脑膜瘤进行鉴别,病理上表现为大小较为一致的细胞无特定的排列方式,胞浆不明显,伴大量小血管腔和致密的网状纤维,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丰富的网状纤维包绕每一个细胞。尽管HPC形成明确的包块,它们仍可以侵犯或破坏周围骨组织。免疫组化中波形蛋白、Leu-7和CD34阳性,结蛋白灶性阳性;与脑膜瘤的区别在于HPC无上皮膜抗原(EMA)阳性细胞,S-100蛋白和典型的内皮细胞抗原如Ⅷ因子相关抗原也为阴性[3]。另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在HPC上调,内皮细胞VEGF受体1和2也上调,提示该肿瘤存在旁分泌的作用模式。
本病最大的特点是容易复发和转移,通常在病灶全切术后的40~70个月内复发,容易转移的部位为骨、肺、肝,在术后15年有64%~68%病例出现转移,通常在诊断后的63~99个月出现远处转移,转移后平均存活时间为2年[4]。本例患者在10余年时间里多次复发,且出现肺和肝等多处转移。肺部转移表现为弥漫分布的大小不等的结节,内部密度均匀,部分可能融合,但纵隔淋巴结通常无肿大,表明这种转移以血道转移为主。PET/CT通常显示原发病灶的FDG18摄取率并无增高表现,而转移病灶的表现报道不一[5]。
目前本病的治疗方案主要为手术切除加局部放疗,手术是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但术中容易出血,也不能防止复发。有报道术前进行肿瘤的栓塞治疗可能有助于减少复发。立体放疗用于控制小肿瘤,包括残存、复发和局部转移的肿瘤,可以延缓复发时间。另外,对于某些较大肿瘤,术前放疗也有助于减少血管通透性,有助于术中彻底清除肿瘤[6]。化疗在本病的地位尚不明确,包括药物的选择、剂量、使用方式以及疗程。阿霉素单独或者联合应用是最有效的方式,有报道12例患者中完全和部分缓解率达50%[6]。随着靶向治疗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关于使用血管生成抑制的药物治疗HPC伴发转移的病例,如Sunitinib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DGFR)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酪氨酸酶抑制剂,具有抗增殖和抗血管的属性,有不少病例报告中都显示其抑制转移灶生长的特性[7]。本病虽然容易复发和转移,表现为恶性肿瘤的特性,但是生存时间却相对较长,如在Mayo临床中心报道了一组38例中枢神经系统的HPC,5年的生存率达93%,5年无病生存率达83%[8]。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45岁。因“声音嘶哑、构音障碍”于2001年就诊于本院。予头颅磁共振(MRI)检查示“枕大孔区占位”,患者拒绝手术治疗。患者到外院行伽玛刀颅脑放射治疗后,症状得到明显缓解。此后每年行头颅MRI复查,显示肿块逐渐缩小。2004年患者再次出现颈部酸胀感,无肢体麻木无力,在外院诊断为“颈椎病”,进行颈椎牵引治疗,症状未得到改善。在本院经头颅MRI检查后示“枕大孔区肿块明显增大,颅外椎管内出现占位病灶,颈静脉孔扩大,局部骨质破坏,内见一实质性软组织肿块影,延椎间孔生长,第1、2颈椎水平椎动脉被肿块包绕,肿块与颈内动脉的间隙尚清晰。患者再次到外院行伽玛刀颅脑放射治疗,但此次症状缓解不明显。既往体健,个人史及家族史无特殊。血常规、生化、血肿瘤指标均正常,胸部X线片、上腹部及泌尿系统B超均正常。2005年4月在本院进行了全身麻醉下的颈椎C1~C3硬脊膜外椎管内肿瘤切除术,术中发现枕大孔与颈1间隙以及颈2~颈3间隙均有肿瘤组织突出椎管,张力增高;颈1和颈2左侧椎板被肿瘤浸润破损。术后病理示血管周细胞瘤。术后7年间患者又进行5次放射治疗和1次伽玛刀治疗,病情尚平稳。
2012年7月25日患者无诱因下突发头晕,伴恶心、呕吐2次,饮水呛咳,无肢体抽搐、耳鸣眩晕、头痛,再次就诊本院。查体:血压118/77 mm Hg(1 mm Hg=0.133 kPa),脉搏96次/min,呼吸20次/min。 神志清楚,步态正常,对答切题。左眼闭合不全,右侧眼睑、口角不自主抽动,眼球活动自如,无眼球震颤;左侧鼻唇沟变浅,口角右歪,伸舌左偏,左侧舌肌萎缩。颈抵抗,克氏征阴性和布氏征阴性。双肺呼吸音粗,两下肺可闻及细小湿啰音。心脏腹部体检正常,四肢肌力和肌张力均正常,病理征阴性。
辅助检查:血常规、生化及肿瘤指标均在正常。上腹部B超检查示肝脏多发低回声团块。甲状腺B超检查示甲状腺右侧叶多发结节。头颅MRI检查示蝶窦、斜坡、岩尖、左侧桥小脑区、颈4平面椎管内硬膜外可见多发肿块影,增强后可见外周强化,内部见不规则扭曲的血管影(图 1)。胸部CT检查示两肺多发结节和肿块影,边缘清楚、内部密度均匀,少数直径>5 cm,以两下肺为主,纵隔淋巴结无肿大(图 2和图 3)。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术获取肺组织,病理显示高密度的肿瘤细胞聚集,大小较一致,细胞间可见扩张血管,其间肿瘤细胞周围有丰富的网状纤维围绕;免疫组化示波形蛋白(+)、CD34(+)、结蛋白灶性(+),EMA(-)、S-100(-),诊断:血管周细胞瘤(图 4和图 5)。临床诊断为颅内血管周细胞瘤复发伴肺和肝脏转移。患者明确诊断后自动出院,随访1年后死亡。
 图1
颅脑MRI检查 a.横断面示颅内多发边界清晰的球形影,增强后可见个带环形强化,内有不规则密度增高的钙化影;b.矢状位
图1
颅脑MRI检查 a.横断面示颅内多发边界清晰的球形影,增强后可见个带环形强化,内有不规则密度增高的钙化影;b.矢状位
 图2
胸部CT检查 肺窗示两肺弥漫分布大小不等类圆形结节影和少量肿块,边界清楚
图2
胸部CT检查 肺窗示两肺弥漫分布大小不等类圆形结节影和少量肿块,边界清楚
 图3
胸部CT检查 纵隔窗示两肺弥漫大小不等结节,密度均匀,与肺窗相比体积略小,纵隔淋巴结无肿大
图3
胸部CT检查 纵隔窗示两肺弥漫大小不等结节,密度均匀,与肺窗相比体积略小,纵隔淋巴结无肿大
 图4
高密度的肿瘤细胞间可见扩张血管(HE ×100)
图4
高密度的肿瘤细胞间可见扩张血管(HE ×100)
 图5
肿瘤细胞和内皮细胞CD34阳性(免疫组化 ×400)
图5
肿瘤细胞和内皮细胞CD34阳性(免疫组化 ×400)
讨论 脑膜血管周细胞瘤(haemangiopericytoma,HPC)是一种少见的中枢神经肿瘤,约占所有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0.4%,其与脑膜瘤的发病率之比为1 ∶40~1 ∶60,平均发病年龄为43岁,男女发病率之比为1.4 ∶1[1]。发病部位主要位于颅内,少数位于脊髓;通常与硬脑脊膜相连。临床表现多样,与病灶的部位相关,部分患者可表现为急性颅内出血。本患者也因肿瘤复发的部位改变而出现不同的临床表现。脑膜HPC在CT和MRI上边界清楚,附于硬脑膜,边缘光滑或呈结节状,增强后可以强化,瘤周存在细胞溶解性骨质破坏,一般无钙化[2]。
脑膜HPC主要需与脑膜瘤进行鉴别,病理上表现为大小较为一致的细胞无特定的排列方式,胞浆不明显,伴大量小血管腔和致密的网状纤维,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丰富的网状纤维包绕每一个细胞。尽管HPC形成明确的包块,它们仍可以侵犯或破坏周围骨组织。免疫组化中波形蛋白、Leu-7和CD34阳性,结蛋白灶性阳性;与脑膜瘤的区别在于HPC无上皮膜抗原(EMA)阳性细胞,S-100蛋白和典型的内皮细胞抗原如Ⅷ因子相关抗原也为阴性[3]。另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在HPC上调,内皮细胞VEGF受体1和2也上调,提示该肿瘤存在旁分泌的作用模式。
本病最大的特点是容易复发和转移,通常在病灶全切术后的40~70个月内复发,容易转移的部位为骨、肺、肝,在术后15年有64%~68%病例出现转移,通常在诊断后的63~99个月出现远处转移,转移后平均存活时间为2年[4]。本例患者在10余年时间里多次复发,且出现肺和肝等多处转移。肺部转移表现为弥漫分布的大小不等的结节,内部密度均匀,部分可能融合,但纵隔淋巴结通常无肿大,表明这种转移以血道转移为主。PET/CT通常显示原发病灶的FDG18摄取率并无增高表现,而转移病灶的表现报道不一[5]。
目前本病的治疗方案主要为手术切除加局部放疗,手术是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但术中容易出血,也不能防止复发。有报道术前进行肿瘤的栓塞治疗可能有助于减少复发。立体放疗用于控制小肿瘤,包括残存、复发和局部转移的肿瘤,可以延缓复发时间。另外,对于某些较大肿瘤,术前放疗也有助于减少血管通透性,有助于术中彻底清除肿瘤[6]。化疗在本病的地位尚不明确,包括药物的选择、剂量、使用方式以及疗程。阿霉素单独或者联合应用是最有效的方式,有报道12例患者中完全和部分缓解率达50%[6]。随着靶向治疗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关于使用血管生成抑制的药物治疗HPC伴发转移的病例,如Sunitinib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DGFR)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酪氨酸酶抑制剂,具有抗增殖和抗血管的属性,有不少病例报告中都显示其抑制转移灶生长的特性[7]。本病虽然容易复发和转移,表现为恶性肿瘤的特性,但是生存时间却相对较长,如在Mayo临床中心报道了一组38例中枢神经系统的HPC,5年的生存率达93%,5年无病生存率达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