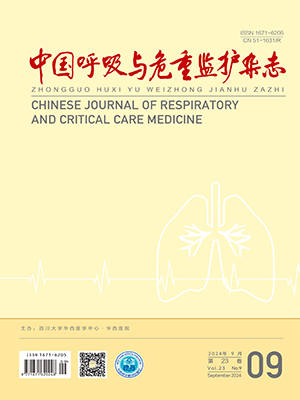引用本文: 赵新成, 史家欣, 梁程程, 李家树. 嗜酸性粒细胞作为生物标志物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8, 17(6): 624-628. doi: 10.7507/1671-6205.201803057 复制
随着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及日益加剧的空气污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将逐年增加,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项目”预计,至 2020 年慢阻肺将位居世界疾病经济负担的第 5 位,并将跃居全球死亡原因的第 3 位[1]。如何有效地防治慢阻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往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嗜酸性粒细胞为哮喘的主要效应细胞之一,伴随对嗜酸性粒细胞功能认识的深入,以及慢阻肺治疗中以“抗炎”为导向的研究积累,嗜酸性粒细胞在慢阻肺病理生理进程中的作用不断被认知,近年来更是被研究者认为可能成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可以指导慢阻肺的治疗和管理。为此本文将对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作为生物标志物在慢阻肺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嗜酸性粒细胞的生理病理学特性
嗜酸性粒细胞是一种先天的自然免疫细胞,占总白细胞的比例不到 5%,其主要在骨髓中形成,并且主要储存在胃肠道和胸腺中,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被募集到肺部,肺脏不是嗜酸性粒细胞的自然寄宿器官,因此它们在肺气道中的存在常提示异常的炎症反应[2-3]。嗜酸性粒细胞既往被普遍认为其主要作用在于变态反应性疾病中的宿主免疫防御和寄生虫感染后免疫[4]。有研究表明,在被病毒感染的小鼠呼吸道模型中嗜酸性粒细胞脱颗粒的数量直接影响到小鼠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病毒的清除[5]。同样在假单胞菌感染的小鼠模型体内实验中发现,通过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的介导使得假单胞菌的清除率大幅度增加,这一发现支持嗜酸性粒细胞具有抗菌特性的观点[6]。
2 生物标志物的定义、慢阻肺生物标志物研究现状与开发
2.1 生物标志物的定义与标准
WHO 将生物标志物定义为:人体或代谢产物中,可以影响或预测特定的结局或疾病发生率的任何可被检测的物质、结构或者过程[7]。随着精准医学[8]和个性化医学概念的提出,生物标志物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一个“理想”的生物标志物的标准是:(1)在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具有生物学上的合理性;(2)要与临床上关键指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3)通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发生改变的指标[9]。良好的生物标志物能够使特定患者的治疗干预更加有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效果,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治疗的风险[8]。
2.2 慢阻肺相关生物标志物研究现状
生物标志物可指导对慢阻肺患者的治疗。例如:当血清 25-OH-VD<10~20 ng/ml 时,补充维生素 D 治疗可以降低中、重度慢阻肺患者的急性加重发生率[10]。Sin[11]和 Obeidat 等[12]研究发现重度慢阻肺患者血清表面活性蛋白 D(surfactant protein D,SP-D)水平与 FEV1 呈显著负相关,血清中 SP-D 可作为慢阻肺致病风险因素,其上调可作为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一个危险信号。气道黏膜壁白三烯受体的数目在慢阻肺稳定期患者中明显增多,而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期则进一步增多[13]。在慢阻肺的模型中发现,作为半胱氨酰白三烯 1 型受体(cysteinyl leukotriene type 1 receptor,CysLT1)拮抗剂的孟鲁司特具有减轻肺气肿和抗炎的作用[14]。慢阻肺是有多种表型的异质性疾病,每种表型分别由一套独特的分子通路驱动。
2.3 慢阻肺生物标志物的开发
诱导痰、肺泡灌洗液、支气管活检标本、呼出气一氧化氮(fraction of exhaled nitric oxide,FeNO)均已被用于发掘慢阻肺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但以上方法存在有创伤性、可重复性差和缺乏标准化的衡量方法等缺点,所以生物标志物发现的重点逐步转移到远离肺组织来源的血液标本上。最新的“肺和小气道芯片”技术(一种仿生微流体细胞培养装置)的出现为慢阻肺的研究诸如:疾病模型,早期检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验证,治疗靶点以及药物疗效评估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15]。目前在慢阻肺研究领域还未得到既定的生物标志物,以满足“理想”生物标志物的标准。研究者须精心设计可行的研究方案,将最有希望的生物标志物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为确保临床相关性,“理想”的生物标志物需解决以下问题[16]:① 出众性:测试会超过当前标准吗?② 可操作性:测试可以改变对患者的管理吗?③ 有价值性:测试会改善患者的预后吗?④ 经济性:测试会减少医保花费吗?⑤ 临床可实施性:生物标志物和分析技术在临床实验室中是否有实施的途径?对上述问题的肯定回答以期能够找到合适的生物标志物指导慢阻肺的治疗,从而应对日益严重的慢阻肺发病趋势。
3 嗜酸性粒细胞在慢阻肺中的研究进展
3.1 嗜酸性粒细胞在慢阻肺急性加重发生风险判断中的价值
第 1 项研究是 WISDOM 研究[17],重度以上稳定期慢阻肺患者接受(噻托溴铵/沙美特罗/氟替卡松,剂量比为:18 μg/100 μg/1 000 μg,用法:1 吸/d)三药联合吸入治疗 6 周后,在 12 周内逐渐停用氟替卡松,以双重支气管舒张剂(噻托溴铵/沙美特罗)为后续治疗,结果未增加中、重度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风险。其中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300 个/μl 或≥4% 的慢阻肺患者占 20%,继续使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ICS)可以降低中、重度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发生率,另外 80% 即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300 个/μl 或<4% 的慢阻肺患者,并未因为使用 ICS 而使急性加重风险降低。
第 2 项研究[18]共纳入 3177 例前一年有≥1 次急性加重史的中、重度慢阻肺患者,以血嗜酸性粒细胞基线百分比 2% 为宽度分层,其中 2083 例(66%)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基线≥2%,纳入患者分别接受为期 12 个月联合用药治疗(维兰特罗 25μg/氟替卡松 50 μg/100 μg/200 μg,用法:1 次/d)和单药治疗(维兰特罗 25 μg,用法:1 次/d)。事后分析发现与维兰特罗单药治疗组相比较,在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2% 的患者中,联合用药组减少急性加重发生率达到 10%,在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2% 的患者中减少急性加重发生率达到 29%(其中各亚组为:2%~4% 亚组 24%,4%~6% 亚组 32%,≥6% 亚组 42%)。
第 3 项是 FLAME 研究[19],该研究比较了茚达特罗/格隆溴铵(110 μg/50 μg,用法:1 吸/d)与沙美特罗/氟替卡松(50 μg/500 μg,用法:2 吸/d)两种治疗方案用于先前一年有≥1 次急性加重史的慢阻肺患者。根据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2% 和≥2%,<3% 和≥3%,<5% 和≥5%)和血嗜酸性粒细胞绝对计数(<150 个/μl,150~300 个/μl,≥300 个/μl)将纳入的患者分成两组及各亚组。事后分析发现茚达特罗/格隆溴铵在用于预防<2%、≥2%、<3%、<5% 和<150 个/μl 等亚组患者的急性加重风险显著优于沙美特罗/氟替卡松。此外,中、重度急性加重的发生率并未随着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增加而增加。在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2% 和≥2% 两个亚组中接受沙美特罗/氟替卡松治疗的患者肺炎发生率高于茚达特罗/格隆溴铵治疗者。
第 4 项研究是 TRIBUTE 研究[20],通过为期 52 周的吸入治疗,比较三联疗法(倍氯米松/福莫特罗/格隆溴铵,剂量比为 87 μg/5 μg/9 μg,用法:2 吸/d)与双支气管舒张剂(茚达特罗/格隆溴铵,剂量比为 85 μg/43 μg,用法:1 吸/d)对研究人群(即尽管使用维持性治疗仍存在严重气流受限症状且前一年至少有一次中度或重度急性加重的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发生率的影响。结果提示以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取 2% 为截断值时,三联疗法组同双支气管舒张剂组相比,显著降低了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2% 的中度、重度慢阻肺患者的急性加重发生率,但未增加肺炎的发生风险。
通过对以上四项大型临床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表明,血嗜酸性粒细胞可以被用作生物标志物来预测哪些患者更容易发生急性加重风险,以及哪些患者对 ICS 治疗反应更佳。但是 Kerkhof 等[21]通过对 8318 例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频率的随访结果提示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可能仅预测吸烟者的慢阻肺急性加重风险。今后仍需进行前瞻性研究来验证血嗜酸性粒细胞对 ICS 治疗效应的预测作用,以及血嗜酸性粒细胞预测急性加重发生风险的阈值,为指导慢阻肺的治疗和管理提供参考价值。
3.2 嗜酸性粒细胞的最佳截断值
在 ECLIPSE 研究[22]的亚组人群分析中发现,慢阻肺患者按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高于 2% 和低于 2% 分为两组,在 3 年的随访时间内,每年抽样一次,发现 51% 的慢阻肺患者的嗜酸性粒细胞计数都保持在或低于 2% 的临界值。Hospers 等[23]发现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定义为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数超过 275 个/μl)全因死亡率风险增加,并且独立于年龄、性别、吸烟习惯及肺功能。哥本哈根总人口流行病学分析研究[24]表明当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340 个/μl 时,慢阻肺急性加重发生率升高 2 倍。高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500 个/μl)甚至可以作为慢阻肺急性加重风险的独立预测因子[25]。
以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 2% 为截断值(约等于 150 个/μl 绝对细胞计数)已被用作大多数研究中的特定阈值[26]。血嗜酸性粒细胞分别以细胞计数百分比 2% 和绝对计数 150 个/μl 为截断值使样本分类的一致性达到 88%[22]。以此阈值在(6 个月或>2 年)的时间点重复测量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结果提示超过 86% 的测量值保持在同一范围内,表明该阈值具有良好的稳定性[27]。最佳截断值还取决于使用境况,比如是预测急性加重风险还是预测对治疗的反应,并且可能需要针对不同观察终点采用不同截断值[28]。对于该使用血嗜酸性粒细胞的相对值还是绝对值来预测慢阻肺患者采用 ICS 治疗的获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3.3 嗜酸性粒细胞指导慢阻肺的糖皮质激素应用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报告[29]显示: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2% 相较于<2% 的慢阻肺患者对口服糖皮质激素(oral corticosteroids,OCS)的症状改善反应更好。Bafadhel 等[30]进一步研究提示:OCS 使得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水平≥200 个/μl 的慢阻肺患者住院时间缩短,并且建议使用在慢阻肺急性加重开始时测量的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作为生物标记物,定向给予 OCS 治疗可以更大限度地提高效益,并更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全身性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使用血嗜酸性粒细胞可以指导 ICS 的治疗选择,Riesbeck[31]在一项交叉临床试验中发现:ICS 组与安慰剂组相比,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患者在使用 ICS 治疗后症状和运动能力的改善比安慰剂组更明显。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2% 的患者,经 ICS 治疗后与安慰剂组相比,肺功能下降明显减弱[32],而 ICS 撤药与 WISDOM 研究[17]结束时肺功能下降幅度增加有关[33]。在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随机试验中发现,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高于 2% 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其全因住院率和慢阻肺相关住院率升高可达 4 倍[34-35]。在高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水平的慢阻肺患者中 ICS 治疗可以显著降低急性加重率[18, 36],显著减少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恢复时间[37],以及更少的治疗失败率[38]。
在慢阻肺的治疗中,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与痰嗜酸性粒细胞有很好的相关性[39]。近期的研究证据强调了痰和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可作为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生物标志物,以及对糖皮质激素或其他抗嗜酸性粒细胞治疗的反应[40-41]。在最近对慢阻肺患者的队列研究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与 10 年随访时死亡风险降低有关[42]。Bafadhel 等[43]对三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纳入了 4 528 例慢阻肺患者)的事后分析发现随着单独接受福莫特罗的慢阻肺患者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增加,急性加重频率亦随之呈非线性增加。当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为 0.1×109/L 或更高时,与单用福莫特罗相比,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对减少急性加重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
对四项大型研究(ISOLDE,INSPIRE,TORCH,SUMMIT)[44-47]的回顾性分析得出如下共识:慢阻肺患者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和更频繁的急性加重相关;ICS 治疗有利于减少高嗜酸性粒细胞水平慢阻肺患者发生急性加重的频率;随着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升高,患者使用 ICS 的临床应答增强。当然 ICS 亦非完美,PATHOS 研究[48]及一项 Meta 分析[49]均提示 ICS 会增加慢阻肺患者并发肺炎的风险,尤其是当慢阻肺患者的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0.34×109/L 时因肺炎住院的风险显著增高[50]。嗜酸性粒细胞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存在一定的变异性[51]。但一项英国初级保健队列研究[52]对 27 557 例稳定期慢阻肺患者评估了 1 年内血液嗜酸性粒细胞水平(每位患者平均 2.2 次血嗜酸性粒细胞检测),数据分析表明血嗜酸性粒细胞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及可重复性。
4 总结与展望
嗜酸性粒细胞作为慢阻肺的生物标志物尚存如下疑问:① 目前广泛建议的以 2% 为嗜酸性粒细胞截断值水平是否正确?实际上在 65% 的健康人和 70% 的慢阻肺患者中都已超过了这个阈值。② 单一的血嗜酸性粒细胞计量是否足以鉴定易感性表型?慢阻肺患者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随时间的稳定性仍需大样本、长时间随访的数据支撑。③ 证据是否足以保证临床实践的改变?迄今为止,尚无大型前瞻性研究评估慢阻肺患者使用血嗜酸性粒细胞阈值作为特定标准的治疗效果。④ 嗜酸性粒细胞究竟是敌是友?嗜酸性粒细胞水平与病情恶化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尚不清楚,抑制普通人群中正常范围内嗜酸性粒细胞水平是否存在风险仍有待观察。
生物标志物可以发展为新的或现有药物的辅助诊断[53],以确定其对特定患者的价值;生物标志物可以通过准确识别最有可能受益的和/或可能受到治疗损害的患者来指导治疗决策;生物标志物还可以告知特定患者的最佳剂量信息。血嗜酸性粒细胞作为一个易于获得的生物标志物,在识别慢阻肺急性发作风险和对糖皮质激素的治疗反应方面具有非常吸引人的潜在价值,但是在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用来识别慢阻肺表型以适应特定的免疫调节治疗之前,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加以证明。
随着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及日益加剧的空气污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将逐年增加,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项目”预计,至 2020 年慢阻肺将位居世界疾病经济负担的第 5 位,并将跃居全球死亡原因的第 3 位[1]。如何有效地防治慢阻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往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嗜酸性粒细胞为哮喘的主要效应细胞之一,伴随对嗜酸性粒细胞功能认识的深入,以及慢阻肺治疗中以“抗炎”为导向的研究积累,嗜酸性粒细胞在慢阻肺病理生理进程中的作用不断被认知,近年来更是被研究者认为可能成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可以指导慢阻肺的治疗和管理。为此本文将对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作为生物标志物在慢阻肺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嗜酸性粒细胞的生理病理学特性
嗜酸性粒细胞是一种先天的自然免疫细胞,占总白细胞的比例不到 5%,其主要在骨髓中形成,并且主要储存在胃肠道和胸腺中,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被募集到肺部,肺脏不是嗜酸性粒细胞的自然寄宿器官,因此它们在肺气道中的存在常提示异常的炎症反应[2-3]。嗜酸性粒细胞既往被普遍认为其主要作用在于变态反应性疾病中的宿主免疫防御和寄生虫感染后免疫[4]。有研究表明,在被病毒感染的小鼠呼吸道模型中嗜酸性粒细胞脱颗粒的数量直接影响到小鼠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病毒的清除[5]。同样在假单胞菌感染的小鼠模型体内实验中发现,通过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的介导使得假单胞菌的清除率大幅度增加,这一发现支持嗜酸性粒细胞具有抗菌特性的观点[6]。
2 生物标志物的定义、慢阻肺生物标志物研究现状与开发
2.1 生物标志物的定义与标准
WHO 将生物标志物定义为:人体或代谢产物中,可以影响或预测特定的结局或疾病发生率的任何可被检测的物质、结构或者过程[7]。随着精准医学[8]和个性化医学概念的提出,生物标志物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一个“理想”的生物标志物的标准是:(1)在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具有生物学上的合理性;(2)要与临床上关键指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3)通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发生改变的指标[9]。良好的生物标志物能够使特定患者的治疗干预更加有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效果,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治疗的风险[8]。
2.2 慢阻肺相关生物标志物研究现状
生物标志物可指导对慢阻肺患者的治疗。例如:当血清 25-OH-VD<10~20 ng/ml 时,补充维生素 D 治疗可以降低中、重度慢阻肺患者的急性加重发生率[10]。Sin[11]和 Obeidat 等[12]研究发现重度慢阻肺患者血清表面活性蛋白 D(surfactant protein D,SP-D)水平与 FEV1 呈显著负相关,血清中 SP-D 可作为慢阻肺致病风险因素,其上调可作为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一个危险信号。气道黏膜壁白三烯受体的数目在慢阻肺稳定期患者中明显增多,而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期则进一步增多[13]。在慢阻肺的模型中发现,作为半胱氨酰白三烯 1 型受体(cysteinyl leukotriene type 1 receptor,CysLT1)拮抗剂的孟鲁司特具有减轻肺气肿和抗炎的作用[14]。慢阻肺是有多种表型的异质性疾病,每种表型分别由一套独特的分子通路驱动。
2.3 慢阻肺生物标志物的开发
诱导痰、肺泡灌洗液、支气管活检标本、呼出气一氧化氮(fraction of exhaled nitric oxide,FeNO)均已被用于发掘慢阻肺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但以上方法存在有创伤性、可重复性差和缺乏标准化的衡量方法等缺点,所以生物标志物发现的重点逐步转移到远离肺组织来源的血液标本上。最新的“肺和小气道芯片”技术(一种仿生微流体细胞培养装置)的出现为慢阻肺的研究诸如:疾病模型,早期检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验证,治疗靶点以及药物疗效评估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15]。目前在慢阻肺研究领域还未得到既定的生物标志物,以满足“理想”生物标志物的标准。研究者须精心设计可行的研究方案,将最有希望的生物标志物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为确保临床相关性,“理想”的生物标志物需解决以下问题[16]:① 出众性:测试会超过当前标准吗?② 可操作性:测试可以改变对患者的管理吗?③ 有价值性:测试会改善患者的预后吗?④ 经济性:测试会减少医保花费吗?⑤ 临床可实施性:生物标志物和分析技术在临床实验室中是否有实施的途径?对上述问题的肯定回答以期能够找到合适的生物标志物指导慢阻肺的治疗,从而应对日益严重的慢阻肺发病趋势。
3 嗜酸性粒细胞在慢阻肺中的研究进展
3.1 嗜酸性粒细胞在慢阻肺急性加重发生风险判断中的价值
第 1 项研究是 WISDOM 研究[17],重度以上稳定期慢阻肺患者接受(噻托溴铵/沙美特罗/氟替卡松,剂量比为:18 μg/100 μg/1 000 μg,用法:1 吸/d)三药联合吸入治疗 6 周后,在 12 周内逐渐停用氟替卡松,以双重支气管舒张剂(噻托溴铵/沙美特罗)为后续治疗,结果未增加中、重度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风险。其中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300 个/μl 或≥4% 的慢阻肺患者占 20%,继续使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ICS)可以降低中、重度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发生率,另外 80% 即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300 个/μl 或<4% 的慢阻肺患者,并未因为使用 ICS 而使急性加重风险降低。
第 2 项研究[18]共纳入 3177 例前一年有≥1 次急性加重史的中、重度慢阻肺患者,以血嗜酸性粒细胞基线百分比 2% 为宽度分层,其中 2083 例(66%)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基线≥2%,纳入患者分别接受为期 12 个月联合用药治疗(维兰特罗 25μg/氟替卡松 50 μg/100 μg/200 μg,用法:1 次/d)和单药治疗(维兰特罗 25 μg,用法:1 次/d)。事后分析发现与维兰特罗单药治疗组相比较,在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2% 的患者中,联合用药组减少急性加重发生率达到 10%,在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2% 的患者中减少急性加重发生率达到 29%(其中各亚组为:2%~4% 亚组 24%,4%~6% 亚组 32%,≥6% 亚组 42%)。
第 3 项是 FLAME 研究[19],该研究比较了茚达特罗/格隆溴铵(110 μg/50 μg,用法:1 吸/d)与沙美特罗/氟替卡松(50 μg/500 μg,用法:2 吸/d)两种治疗方案用于先前一年有≥1 次急性加重史的慢阻肺患者。根据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2% 和≥2%,<3% 和≥3%,<5% 和≥5%)和血嗜酸性粒细胞绝对计数(<150 个/μl,150~300 个/μl,≥300 个/μl)将纳入的患者分成两组及各亚组。事后分析发现茚达特罗/格隆溴铵在用于预防<2%、≥2%、<3%、<5% 和<150 个/μl 等亚组患者的急性加重风险显著优于沙美特罗/氟替卡松。此外,中、重度急性加重的发生率并未随着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增加而增加。在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2% 和≥2% 两个亚组中接受沙美特罗/氟替卡松治疗的患者肺炎发生率高于茚达特罗/格隆溴铵治疗者。
第 4 项研究是 TRIBUTE 研究[20],通过为期 52 周的吸入治疗,比较三联疗法(倍氯米松/福莫特罗/格隆溴铵,剂量比为 87 μg/5 μg/9 μg,用法:2 吸/d)与双支气管舒张剂(茚达特罗/格隆溴铵,剂量比为 85 μg/43 μg,用法:1 吸/d)对研究人群(即尽管使用维持性治疗仍存在严重气流受限症状且前一年至少有一次中度或重度急性加重的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发生率的影响。结果提示以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取 2% 为截断值时,三联疗法组同双支气管舒张剂组相比,显著降低了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2% 的中度、重度慢阻肺患者的急性加重发生率,但未增加肺炎的发生风险。
通过对以上四项大型临床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表明,血嗜酸性粒细胞可以被用作生物标志物来预测哪些患者更容易发生急性加重风险,以及哪些患者对 ICS 治疗反应更佳。但是 Kerkhof 等[21]通过对 8318 例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频率的随访结果提示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可能仅预测吸烟者的慢阻肺急性加重风险。今后仍需进行前瞻性研究来验证血嗜酸性粒细胞对 ICS 治疗效应的预测作用,以及血嗜酸性粒细胞预测急性加重发生风险的阈值,为指导慢阻肺的治疗和管理提供参考价值。
3.2 嗜酸性粒细胞的最佳截断值
在 ECLIPSE 研究[22]的亚组人群分析中发现,慢阻肺患者按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高于 2% 和低于 2% 分为两组,在 3 年的随访时间内,每年抽样一次,发现 51% 的慢阻肺患者的嗜酸性粒细胞计数都保持在或低于 2% 的临界值。Hospers 等[23]发现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定义为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数超过 275 个/μl)全因死亡率风险增加,并且独立于年龄、性别、吸烟习惯及肺功能。哥本哈根总人口流行病学分析研究[24]表明当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340 个/μl 时,慢阻肺急性加重发生率升高 2 倍。高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500 个/μl)甚至可以作为慢阻肺急性加重风险的独立预测因子[25]。
以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 2% 为截断值(约等于 150 个/μl 绝对细胞计数)已被用作大多数研究中的特定阈值[26]。血嗜酸性粒细胞分别以细胞计数百分比 2% 和绝对计数 150 个/μl 为截断值使样本分类的一致性达到 88%[22]。以此阈值在(6 个月或>2 年)的时间点重复测量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结果提示超过 86% 的测量值保持在同一范围内,表明该阈值具有良好的稳定性[27]。最佳截断值还取决于使用境况,比如是预测急性加重风险还是预测对治疗的反应,并且可能需要针对不同观察终点采用不同截断值[28]。对于该使用血嗜酸性粒细胞的相对值还是绝对值来预测慢阻肺患者采用 ICS 治疗的获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3.3 嗜酸性粒细胞指导慢阻肺的糖皮质激素应用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报告[29]显示: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2% 相较于<2% 的慢阻肺患者对口服糖皮质激素(oral corticosteroids,OCS)的症状改善反应更好。Bafadhel 等[30]进一步研究提示:OCS 使得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水平≥200 个/μl 的慢阻肺患者住院时间缩短,并且建议使用在慢阻肺急性加重开始时测量的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作为生物标记物,定向给予 OCS 治疗可以更大限度地提高效益,并更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全身性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使用血嗜酸性粒细胞可以指导 ICS 的治疗选择,Riesbeck[31]在一项交叉临床试验中发现:ICS 组与安慰剂组相比,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患者在使用 ICS 治疗后症状和运动能力的改善比安慰剂组更明显。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2% 的患者,经 ICS 治疗后与安慰剂组相比,肺功能下降明显减弱[32],而 ICS 撤药与 WISDOM 研究[17]结束时肺功能下降幅度增加有关[33]。在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随机试验中发现,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高于 2% 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其全因住院率和慢阻肺相关住院率升高可达 4 倍[34-35]。在高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水平的慢阻肺患者中 ICS 治疗可以显著降低急性加重率[18, 36],显著减少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恢复时间[37],以及更少的治疗失败率[38]。
在慢阻肺的治疗中,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与痰嗜酸性粒细胞有很好的相关性[39]。近期的研究证据强调了痰和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可作为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生物标志物,以及对糖皮质激素或其他抗嗜酸性粒细胞治疗的反应[40-41]。在最近对慢阻肺患者的队列研究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与 10 年随访时死亡风险降低有关[42]。Bafadhel 等[43]对三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纳入了 4 528 例慢阻肺患者)的事后分析发现随着单独接受福莫特罗的慢阻肺患者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增加,急性加重频率亦随之呈非线性增加。当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为 0.1×109/L 或更高时,与单用福莫特罗相比,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对减少急性加重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
对四项大型研究(ISOLDE,INSPIRE,TORCH,SUMMIT)[44-47]的回顾性分析得出如下共识:慢阻肺患者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和更频繁的急性加重相关;ICS 治疗有利于减少高嗜酸性粒细胞水平慢阻肺患者发生急性加重的频率;随着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升高,患者使用 ICS 的临床应答增强。当然 ICS 亦非完美,PATHOS 研究[48]及一项 Meta 分析[49]均提示 ICS 会增加慢阻肺患者并发肺炎的风险,尤其是当慢阻肺患者的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0.34×109/L 时因肺炎住院的风险显著增高[50]。嗜酸性粒细胞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存在一定的变异性[51]。但一项英国初级保健队列研究[52]对 27 557 例稳定期慢阻肺患者评估了 1 年内血液嗜酸性粒细胞水平(每位患者平均 2.2 次血嗜酸性粒细胞检测),数据分析表明血嗜酸性粒细胞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及可重复性。
4 总结与展望
嗜酸性粒细胞作为慢阻肺的生物标志物尚存如下疑问:① 目前广泛建议的以 2% 为嗜酸性粒细胞截断值水平是否正确?实际上在 65% 的健康人和 70% 的慢阻肺患者中都已超过了这个阈值。② 单一的血嗜酸性粒细胞计量是否足以鉴定易感性表型?慢阻肺患者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随时间的稳定性仍需大样本、长时间随访的数据支撑。③ 证据是否足以保证临床实践的改变?迄今为止,尚无大型前瞻性研究评估慢阻肺患者使用血嗜酸性粒细胞阈值作为特定标准的治疗效果。④ 嗜酸性粒细胞究竟是敌是友?嗜酸性粒细胞水平与病情恶化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尚不清楚,抑制普通人群中正常范围内嗜酸性粒细胞水平是否存在风险仍有待观察。
生物标志物可以发展为新的或现有药物的辅助诊断[53],以确定其对特定患者的价值;生物标志物可以通过准确识别最有可能受益的和/或可能受到治疗损害的患者来指导治疗决策;生物标志物还可以告知特定患者的最佳剂量信息。血嗜酸性粒细胞作为一个易于获得的生物标志物,在识别慢阻肺急性发作风险和对糖皮质激素的治疗反应方面具有非常吸引人的潜在价值,但是在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用来识别慢阻肺表型以适应特定的免疫调节治疗之前,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