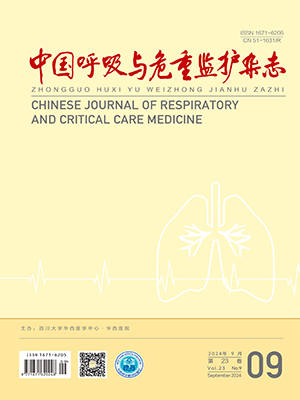引用本文: 夏婷婷, 邵成杰, 史家欣, 李家树. 肺脏固有免疫在革兰阴性菌感染中的作用及研究进展.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2, 21(1): 62-65. doi: 10.7507/1671-6205.202108074 复制
肺脏是特殊的人体器官,它与外界环境直接相通,极易成为病原菌入侵的直接靶器官而造成肺部感染。近年来,随着人口老年化的不断加剧,肺部感染发生率逐年攀升,尤其是因肺部革兰阴性(Gram-negative,G–)菌感染患者发生率和病死率都显著增加。而G–菌(如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是导致肺部感染的重要病原菌,其致病性主要与外膜脂质成分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有关,有研究表明,由7个脂多糖运输蛋白构成的脂多糖运输系统是其发挥致病作用的重要结构基础[1]。G–菌耐药率高、易定植、治疗难度大等特点使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肺脏固有免疫是机体抵御致病菌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有效地为机体提供了局部免疫力,在发生肺部G–菌感染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了解肺脏固有免疫系统在G–菌感染中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寻找新的干预靶点,对临床干预G–菌感染具有重要意义。现就肺脏固有免疫、固有免疫细胞的分类,以及各免疫细胞在G–菌感染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综述。
1 肺脏固有免疫及其细胞分类
肺脏固有免疫系统由固有免疫细胞和固有免疫分子构成,受多种分子信号通路调控。模式分子与细胞膜表面的模式分子识别受体[如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NOD样受体(NOD-like receptor,NLR)、C型凝集素受体、维甲酸诱导基因I样受体等]结合是启动固有免疫反应的关键,根据危险信号的不同可分为病原体相关模式分子、微生物相关模式分子以及损伤或危险相关分子模式分子三类[2]。与适应性免疫相比,固有免疫不需预先致敏、暴露即可直接攻击外来致病菌,具有快速、高效、非特异性等特点,并对协调随后的适应性免疫反应具有重要意义。肺脏固有免疫细胞主要包括气道上皮细胞(alveolar epithelial cell,AEC)、固有淋巴样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ILC)、中性粒细胞(polymorphonuclear neutrophil,PMN)、肺泡巨噬细胞(alveolar macrophage,AM)、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及其他免疫细胞等[3]。不同细胞系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通过释放和接收多种分子信号进行信息交流,共同维持肺脏固有免疫的稳态[4]。
2 各类固有免疫细胞在G–菌感染中的作用
2.1 AEC
在人体和外界环境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的约100 m2的细胞结构—AEC,我们可视其为具有免疫活性的机械屏障。基于功能不同可将AEC分为Ⅰ型和Ⅱ型两种亚群。Ⅰ型AEC主要参与气血屏障的形成,其特殊的薄且宽的结构特征有利于机体进行气体交换。Ⅱ型AEC是肺脏分泌功能的主要承担者,其主要作用是通过调节细胞旁通量、细胞间通讯、黏蛋白的产生及各种细胞因子的分泌,招募免疫细胞聚集和激活白细胞介导的炎症防御系统,此外在其基底外侧还可分泌修复酶,有利于机体免疫稳态的恢复[5]。
在LPS刺激下,病原体相关模式分子与AEC表面TLR、NLR识别,触发下游髓样分化因子88和β干扰素TIR结构域衔接蛋白依赖的信号通路,促进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s,MAPK)、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6的转录,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IL-8等促炎因子大量释放,NOD样受体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炎性小体被激活,引起一系列炎症级联反应[3, 6]。
AEC顶端分泌的黏蛋白(如MUC5AC、MUC5B、MUC1等)广泛存在于AEC表面,是黏液保护层的重要组成成分,不但可限制致病菌的感染和定植,而且还对肺脏炎症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有研究表明,黏蛋白家族中的MUC1可通过抑制TLR信号表达及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负性调节免疫应答,避免过强炎症反应对机体的损害[7]。此外,连接蛋白(connexin,Cx)43介导AEC与表达CD11c的AM形成缝隙连接,这些缝隙连接允许Ca2+信号波在AMs与AEC之间双向传播,在LPS刺激下可观察到两种细胞类型中均存在周期且同步的钙峰值。这支持了AEC缝隙连接通道的双向抗炎作用[8]。再者,依赖于“拉链”和“触发”两种模式的AEC吞噬作用(亦称为“内化”作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在GTP酶Rac-1的介导下,AEC在吞噬细胞碎片、分解产物、凋亡细胞、病原菌等的同时还可分泌大量抗炎细胞因子,以抑制炎症招募和恢复肺脏内环境稳态[9]。基于这些作用,AEC在炎症的发展和解除中均具有重要地位。
2.2 ILC
ILC是近年新发现的一类存在于黏膜表面的辅助性淋巴细胞,在2013年被正式统一提议命名,在固有免疫反应中亦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效应功能和转录需求的差异可将ILC分为ILC1、ILC2、ILC3三组[10]。
2.2.1 ILC1
ILC1是包含具有细胞毒性的NK细胞的一组细胞,是肺部感染早期干扰素(interferon,IFN)-γ、TNF的主要来源[11]。在G–菌感染时,T-box转录因子T-bet发生转录,在多种细胞因子IL-1、IL-6、IL-12、IL-18的介导下,ILC1被激活,TNF、IFN-γ被大量分泌、堆积,IFN-γ促进了趋化因子CXC10、IL-12的释放,招募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迁移至感染部位,在促炎细胞因子TNF的协调作用下,共同促进病原菌的清除[12-14]。
2.2.2 ILC2
ILC2具有分泌细胞因子IL-4、IL-5、IL-6、IL-9和IL-13的能力,主要参与Th2型免疫反应[15],还可在特殊化学因子作用下表现出ILC1、ILC3的细胞特性,参与机体肺脏固有免疫反应。Bal等[16]研究表明,AEC分泌的IL-1β可在IL-12介导下使ILC2具有表达IFN-γ、TNF的能力,表现出ILC1的细胞特性,从而激活促炎反应链。Silver等[17]研究发现,在合并流感嗜血杆菌肺部感染时,细胞因子IFN-γ水平和ILC1样细胞的数目显著增加,证明了ILC2的可塑性。ILC2亦可在IL-25介导下高表达IL-17,而IL-17作为肺脏固有免疫系统重要促炎性细胞因子,可刺激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趋化因子CXCL-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2等细胞因子产生,招募PMN至炎症部位,表现出与ILC3相似的功能特征[18]。
2.2.3 ILC3
ILC3是产生IL-17、IL-22的重要免疫细胞,其对G–菌的清除具有关键作用[19]。Xiong等[20]发现,单核细胞诱导局部细胞因子TNF产生增多,趋化因子CCL20的表达增强,ILC3大量被招募,诱导ILC3分泌细胞因子IL-17并与炎性单核细胞表面的IL-17受体结合,进一步增强炎性单核细胞的抗菌活性,ILC3与炎性单核细胞之间构成了正反馈回路,二者协同抵御病原菌感染。
2.3 PMN
PMN具有较强的趋化作用,是固有免疫的主要吞噬细胞和最终效应细胞。PMN的膜表面可表达多种受体(如趋化因子受体、IgGFc受体和补体C3受体),有研究表明,在LPS的刺激下,趋化因子受体与配体快速结合,IgGFc受体和补体C3受体两者协同促进其趋化速度,招募中性粒细胞更加准确、快速抵达“受伤部位”,直接或间接介导炎症反应[21]。值得注意的是,PMN细胞膜上的趋化因子受体是G蛋白偶联的跨膜受体,通常可与多种趋化因子结合(如CXCR2趋化因子受体与CXCL1、8、2、3、6、7趋化因子等均可结合),在CD18、β2整合素作用下,PMN大量浸润,通过产生活性氧,形成PMN胞外陷阱,并释放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杀菌肽,从而吞噬病原菌及细胞碎片[3]。PMN的浸润过程是固有免疫反应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吞噬致病菌后的PMN会迅速凋亡,其凋亡过程受多基因、多因子共同调控。Wang等[22]通过在小鼠气管内注射LPS构建肺部感染动物模型,再肌注TANK结合激酶1抑制剂进行干预,发现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RIPK)1、RIPK3和混合系列蛋白激酶结构域蛋白(mixed 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 protein,MLKL)的磷酸化增强,并促进了RIPK1-RIPK3-MLKL坏死小体复合物的形成,促进PMN凋亡。最近有学者提出,胞质中的核转录因子NF-κB在PMN凋亡中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但其中的具体作用通路尚未阐明[23]。由此可见,这些调节因子可能是干预PMN凋亡及治疗炎症的靶点。
2.4 AM
AM是人体“常驻边防细胞”,广泛存在于肺泡腔内,其可根据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极化。在正常人体肺脏中普遍表现为M0型,当发生肺部感染时可极化为M1型和M2型,并赋予特定功能,这两种表型之间可相互转换[24]。在G–菌感染过程中,各型AM均扮演了重要角色,M1型AM主要发挥促炎作用,促进病原体的清除;M2型AM主要在炎症反应终末期发挥抗炎和组织修复作用,下调M1型的免疫应答,并加快受损组织的修复。
AM在LPS刺激下可由M0型极化为M1型,高表达促炎细胞因子(如IL-6、IL-8、IL-1β、TNF-α、CC趋化因子配体2、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等),并招募其他免疫细胞聚集,达到快速消灭病原体的目的[25]。再者,AM表面的受体与目标病原体或死亡细胞上的配体分子Fc区域结合,吞噬小体形成并与溶酶体融合,目标病原体或死亡细胞也可被快速吞噬消灭[26]。Nepal等[27]研究发现,在LPS感染的ALI小鼠模型中,细胞因子IL-4和吞噬配体基因6的水平明显升高,二者协同激活转录因子6,促使M1型AM向M2型AM的极化。而M2型AM通过分泌抗炎细胞因子IL-10,激活转录因子4,抑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靶点的活性,维持体内免疫平衡[28]。最后,脂毒素A4激动剂通过激活MAPK-1和MAPK-8信号通路转导,诱导AM产生自噬作用,AM的自噬过程受胰岛素通路、雷帕霉素通路等调控,将已受病原体感染、功能受损的AM降解死亡,对G–菌感染中的肺组织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29]。在G–菌感染过程中,不可控的促炎反应往往会适得其反。Xiong等[30]研究发现巨噬细胞产生过量的炎性细胞因子IL-1β会抑制VE-钙黏合素的转录,增加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破坏内皮细胞屏障的完整性,参与血管损伤,甚至诱发脓毒症的产生,极大地增加了疾病的治疗难度。
2.5 DC
DC是介导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之间的桥梁,是一类重要的抗原提呈细胞,不但可通过特异性的表面受体(如内吞受体、吞噬受体和C型凝集素受体)吸收抗原,而且还配备了多种模式识别受体,以感知不同的危险信号[31-32]。DC被激活,上调共刺激分子,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吸收抗原并处理它,并迁移到淋巴结,在那里它们将抗原提呈给CD8和CD4 T细胞。当发生G–菌感染时,固有免疫被激活,DC会增加与抗原提呈和定向迁移相关的细胞表面分子(趋化因子7受体)的表达,在趋化因子CCL19、CCL21以及Cx43信号通道的介导下,DC被活化并吸收抗原,而后迁移至区域淋巴结[33],将抗原提呈给CD4和CD8 T淋巴细胞,同时产生细胞因子IL-6、IL-10,诱导Th1、Th2或Th17亚群的极化[34],激活宿主适应性免疫反应,致病菌得以清除。Granot等[35]通过对淋巴和黏膜组织DC的分析,证明DC可分泌较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IL-6、IL-8,诱导宿主促炎反应产生。最新有研究表明,泛连接蛋白(pannexin,Panx)1通道可能有助于DC招募和迁移的早期阶段,而包括趋化因子7受体依赖性趋化在内的后期阶段主要依赖于Cx的活性。Cx和Panx之间介导DC迁移的功能区别可能归因于质膜上不同的转换蛋白[36]。DC对维持人体肺脏免疫稳态至关重要,但由于实验数据有限,大多数结果都是通过小鼠DC生物学中推测出来的,因此在维持人体肺脏免疫稳态中各亚群的确切作用尚不十分明确[32]。
3 各类固有免疫细胞之间的交叉联系
肺脏固有免疫功能的整合主要依赖于各型固有免疫细胞系间精致、多样和重叠的作用机制以及细胞间直接或间接的信号交流。在G–菌感染初期,AEC对致病菌高度感知,DC的活化也为后续适应性免疫的激活埋下伏笔。随着病程的进展,ILC、AM产生大量促炎细胞因子,同时PMN被招募至受伤部位,PMN联合AM发挥强大的吞噬作用,杀灭病原体。感染末期,各免疫细胞通过分泌抑炎细胞因子及修复因子对受伤部位进行有效的组织修复,最大程度的恢复肺功能。最终的结果是构建一个复杂、精致的网络系统来维持肺脏免疫稳态。
4 小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各种肺脏固有免疫细胞都对G–菌感染的清除具有重要作用。固有免疫细胞是抵抗肺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并可诱导适应性免疫系统的激活,但在消灭病原体时这些固有免疫细胞常产生过强的炎症反应甚至导致急性肺损伤,因而可将肺脏固有免疫视为一把“双刃剑”,其既是宿主防御的必要条件,也是发病机制的驱动因素,环境与机体的相互影响往往决定了它们的确切作用[2]。随着抗菌药物的进一步使用,多重耐药G–菌层出不穷,传统抗菌药物的疗效不能满足临床需要,因此了解固有免疫在G–菌感染中的作用,有望为临床干预G–菌感染提供新思路。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肺脏是特殊的人体器官,它与外界环境直接相通,极易成为病原菌入侵的直接靶器官而造成肺部感染。近年来,随着人口老年化的不断加剧,肺部感染发生率逐年攀升,尤其是因肺部革兰阴性(Gram-negative,G–)菌感染患者发生率和病死率都显著增加。而G–菌(如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是导致肺部感染的重要病原菌,其致病性主要与外膜脂质成分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有关,有研究表明,由7个脂多糖运输蛋白构成的脂多糖运输系统是其发挥致病作用的重要结构基础[1]。G–菌耐药率高、易定植、治疗难度大等特点使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肺脏固有免疫是机体抵御致病菌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有效地为机体提供了局部免疫力,在发生肺部G–菌感染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了解肺脏固有免疫系统在G–菌感染中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寻找新的干预靶点,对临床干预G–菌感染具有重要意义。现就肺脏固有免疫、固有免疫细胞的分类,以及各免疫细胞在G–菌感染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综述。
1 肺脏固有免疫及其细胞分类
肺脏固有免疫系统由固有免疫细胞和固有免疫分子构成,受多种分子信号通路调控。模式分子与细胞膜表面的模式分子识别受体[如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NOD样受体(NOD-like receptor,NLR)、C型凝集素受体、维甲酸诱导基因I样受体等]结合是启动固有免疫反应的关键,根据危险信号的不同可分为病原体相关模式分子、微生物相关模式分子以及损伤或危险相关分子模式分子三类[2]。与适应性免疫相比,固有免疫不需预先致敏、暴露即可直接攻击外来致病菌,具有快速、高效、非特异性等特点,并对协调随后的适应性免疫反应具有重要意义。肺脏固有免疫细胞主要包括气道上皮细胞(alveolar epithelial cell,AEC)、固有淋巴样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ILC)、中性粒细胞(polymorphonuclear neutrophil,PMN)、肺泡巨噬细胞(alveolar macrophage,AM)、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及其他免疫细胞等[3]。不同细胞系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通过释放和接收多种分子信号进行信息交流,共同维持肺脏固有免疫的稳态[4]。
2 各类固有免疫细胞在G–菌感染中的作用
2.1 AEC
在人体和外界环境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的约100 m2的细胞结构—AEC,我们可视其为具有免疫活性的机械屏障。基于功能不同可将AEC分为Ⅰ型和Ⅱ型两种亚群。Ⅰ型AEC主要参与气血屏障的形成,其特殊的薄且宽的结构特征有利于机体进行气体交换。Ⅱ型AEC是肺脏分泌功能的主要承担者,其主要作用是通过调节细胞旁通量、细胞间通讯、黏蛋白的产生及各种细胞因子的分泌,招募免疫细胞聚集和激活白细胞介导的炎症防御系统,此外在其基底外侧还可分泌修复酶,有利于机体免疫稳态的恢复[5]。
在LPS刺激下,病原体相关模式分子与AEC表面TLR、NLR识别,触发下游髓样分化因子88和β干扰素TIR结构域衔接蛋白依赖的信号通路,促进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s,MAPK)、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6的转录,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IL-8等促炎因子大量释放,NOD样受体蛋白3(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炎性小体被激活,引起一系列炎症级联反应[3, 6]。
AEC顶端分泌的黏蛋白(如MUC5AC、MUC5B、MUC1等)广泛存在于AEC表面,是黏液保护层的重要组成成分,不但可限制致病菌的感染和定植,而且还对肺脏炎症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有研究表明,黏蛋白家族中的MUC1可通过抑制TLR信号表达及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负性调节免疫应答,避免过强炎症反应对机体的损害[7]。此外,连接蛋白(connexin,Cx)43介导AEC与表达CD11c的AM形成缝隙连接,这些缝隙连接允许Ca2+信号波在AMs与AEC之间双向传播,在LPS刺激下可观察到两种细胞类型中均存在周期且同步的钙峰值。这支持了AEC缝隙连接通道的双向抗炎作用[8]。再者,依赖于“拉链”和“触发”两种模式的AEC吞噬作用(亦称为“内化”作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在GTP酶Rac-1的介导下,AEC在吞噬细胞碎片、分解产物、凋亡细胞、病原菌等的同时还可分泌大量抗炎细胞因子,以抑制炎症招募和恢复肺脏内环境稳态[9]。基于这些作用,AEC在炎症的发展和解除中均具有重要地位。
2.2 ILC
ILC是近年新发现的一类存在于黏膜表面的辅助性淋巴细胞,在2013年被正式统一提议命名,在固有免疫反应中亦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效应功能和转录需求的差异可将ILC分为ILC1、ILC2、ILC3三组[10]。
2.2.1 ILC1
ILC1是包含具有细胞毒性的NK细胞的一组细胞,是肺部感染早期干扰素(interferon,IFN)-γ、TNF的主要来源[11]。在G–菌感染时,T-box转录因子T-bet发生转录,在多种细胞因子IL-1、IL-6、IL-12、IL-18的介导下,ILC1被激活,TNF、IFN-γ被大量分泌、堆积,IFN-γ促进了趋化因子CXC10、IL-12的释放,招募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迁移至感染部位,在促炎细胞因子TNF的协调作用下,共同促进病原菌的清除[12-14]。
2.2.2 ILC2
ILC2具有分泌细胞因子IL-4、IL-5、IL-6、IL-9和IL-13的能力,主要参与Th2型免疫反应[15],还可在特殊化学因子作用下表现出ILC1、ILC3的细胞特性,参与机体肺脏固有免疫反应。Bal等[16]研究表明,AEC分泌的IL-1β可在IL-12介导下使ILC2具有表达IFN-γ、TNF的能力,表现出ILC1的细胞特性,从而激活促炎反应链。Silver等[17]研究发现,在合并流感嗜血杆菌肺部感染时,细胞因子IFN-γ水平和ILC1样细胞的数目显著增加,证明了ILC2的可塑性。ILC2亦可在IL-25介导下高表达IL-17,而IL-17作为肺脏固有免疫系统重要促炎性细胞因子,可刺激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趋化因子CXCL-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2等细胞因子产生,招募PMN至炎症部位,表现出与ILC3相似的功能特征[18]。
2.2.3 ILC3
ILC3是产生IL-17、IL-22的重要免疫细胞,其对G–菌的清除具有关键作用[19]。Xiong等[20]发现,单核细胞诱导局部细胞因子TNF产生增多,趋化因子CCL20的表达增强,ILC3大量被招募,诱导ILC3分泌细胞因子IL-17并与炎性单核细胞表面的IL-17受体结合,进一步增强炎性单核细胞的抗菌活性,ILC3与炎性单核细胞之间构成了正反馈回路,二者协同抵御病原菌感染。
2.3 PMN
PMN具有较强的趋化作用,是固有免疫的主要吞噬细胞和最终效应细胞。PMN的膜表面可表达多种受体(如趋化因子受体、IgGFc受体和补体C3受体),有研究表明,在LPS的刺激下,趋化因子受体与配体快速结合,IgGFc受体和补体C3受体两者协同促进其趋化速度,招募中性粒细胞更加准确、快速抵达“受伤部位”,直接或间接介导炎症反应[21]。值得注意的是,PMN细胞膜上的趋化因子受体是G蛋白偶联的跨膜受体,通常可与多种趋化因子结合(如CXCR2趋化因子受体与CXCL1、8、2、3、6、7趋化因子等均可结合),在CD18、β2整合素作用下,PMN大量浸润,通过产生活性氧,形成PMN胞外陷阱,并释放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杀菌肽,从而吞噬病原菌及细胞碎片[3]。PMN的浸润过程是固有免疫反应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吞噬致病菌后的PMN会迅速凋亡,其凋亡过程受多基因、多因子共同调控。Wang等[22]通过在小鼠气管内注射LPS构建肺部感染动物模型,再肌注TANK结合激酶1抑制剂进行干预,发现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RIPK)1、RIPK3和混合系列蛋白激酶结构域蛋白(mixed 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 protein,MLKL)的磷酸化增强,并促进了RIPK1-RIPK3-MLKL坏死小体复合物的形成,促进PMN凋亡。最近有学者提出,胞质中的核转录因子NF-κB在PMN凋亡中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但其中的具体作用通路尚未阐明[23]。由此可见,这些调节因子可能是干预PMN凋亡及治疗炎症的靶点。
2.4 AM
AM是人体“常驻边防细胞”,广泛存在于肺泡腔内,其可根据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极化。在正常人体肺脏中普遍表现为M0型,当发生肺部感染时可极化为M1型和M2型,并赋予特定功能,这两种表型之间可相互转换[24]。在G–菌感染过程中,各型AM均扮演了重要角色,M1型AM主要发挥促炎作用,促进病原体的清除;M2型AM主要在炎症反应终末期发挥抗炎和组织修复作用,下调M1型的免疫应答,并加快受损组织的修复。
AM在LPS刺激下可由M0型极化为M1型,高表达促炎细胞因子(如IL-6、IL-8、IL-1β、TNF-α、CC趋化因子配体2、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等),并招募其他免疫细胞聚集,达到快速消灭病原体的目的[25]。再者,AM表面的受体与目标病原体或死亡细胞上的配体分子Fc区域结合,吞噬小体形成并与溶酶体融合,目标病原体或死亡细胞也可被快速吞噬消灭[26]。Nepal等[27]研究发现,在LPS感染的ALI小鼠模型中,细胞因子IL-4和吞噬配体基因6的水平明显升高,二者协同激活转录因子6,促使M1型AM向M2型AM的极化。而M2型AM通过分泌抗炎细胞因子IL-10,激活转录因子4,抑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靶点的活性,维持体内免疫平衡[28]。最后,脂毒素A4激动剂通过激活MAPK-1和MAPK-8信号通路转导,诱导AM产生自噬作用,AM的自噬过程受胰岛素通路、雷帕霉素通路等调控,将已受病原体感染、功能受损的AM降解死亡,对G–菌感染中的肺组织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29]。在G–菌感染过程中,不可控的促炎反应往往会适得其反。Xiong等[30]研究发现巨噬细胞产生过量的炎性细胞因子IL-1β会抑制VE-钙黏合素的转录,增加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破坏内皮细胞屏障的完整性,参与血管损伤,甚至诱发脓毒症的产生,极大地增加了疾病的治疗难度。
2.5 DC
DC是介导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之间的桥梁,是一类重要的抗原提呈细胞,不但可通过特异性的表面受体(如内吞受体、吞噬受体和C型凝集素受体)吸收抗原,而且还配备了多种模式识别受体,以感知不同的危险信号[31-32]。DC被激活,上调共刺激分子,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吸收抗原并处理它,并迁移到淋巴结,在那里它们将抗原提呈给CD8和CD4 T细胞。当发生G–菌感染时,固有免疫被激活,DC会增加与抗原提呈和定向迁移相关的细胞表面分子(趋化因子7受体)的表达,在趋化因子CCL19、CCL21以及Cx43信号通道的介导下,DC被活化并吸收抗原,而后迁移至区域淋巴结[33],将抗原提呈给CD4和CD8 T淋巴细胞,同时产生细胞因子IL-6、IL-10,诱导Th1、Th2或Th17亚群的极化[34],激活宿主适应性免疫反应,致病菌得以清除。Granot等[35]通过对淋巴和黏膜组织DC的分析,证明DC可分泌较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IL-6、IL-8,诱导宿主促炎反应产生。最新有研究表明,泛连接蛋白(pannexin,Panx)1通道可能有助于DC招募和迁移的早期阶段,而包括趋化因子7受体依赖性趋化在内的后期阶段主要依赖于Cx的活性。Cx和Panx之间介导DC迁移的功能区别可能归因于质膜上不同的转换蛋白[36]。DC对维持人体肺脏免疫稳态至关重要,但由于实验数据有限,大多数结果都是通过小鼠DC生物学中推测出来的,因此在维持人体肺脏免疫稳态中各亚群的确切作用尚不十分明确[32]。
3 各类固有免疫细胞之间的交叉联系
肺脏固有免疫功能的整合主要依赖于各型固有免疫细胞系间精致、多样和重叠的作用机制以及细胞间直接或间接的信号交流。在G–菌感染初期,AEC对致病菌高度感知,DC的活化也为后续适应性免疫的激活埋下伏笔。随着病程的进展,ILC、AM产生大量促炎细胞因子,同时PMN被招募至受伤部位,PMN联合AM发挥强大的吞噬作用,杀灭病原体。感染末期,各免疫细胞通过分泌抑炎细胞因子及修复因子对受伤部位进行有效的组织修复,最大程度的恢复肺功能。最终的结果是构建一个复杂、精致的网络系统来维持肺脏免疫稳态。
4 小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各种肺脏固有免疫细胞都对G–菌感染的清除具有重要作用。固有免疫细胞是抵抗肺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并可诱导适应性免疫系统的激活,但在消灭病原体时这些固有免疫细胞常产生过强的炎症反应甚至导致急性肺损伤,因而可将肺脏固有免疫视为一把“双刃剑”,其既是宿主防御的必要条件,也是发病机制的驱动因素,环境与机体的相互影响往往决定了它们的确切作用[2]。随着抗菌药物的进一步使用,多重耐药G–菌层出不穷,传统抗菌药物的疗效不能满足临床需要,因此了解固有免疫在G–菌感染中的作用,有望为临床干预G–菌感染提供新思路。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